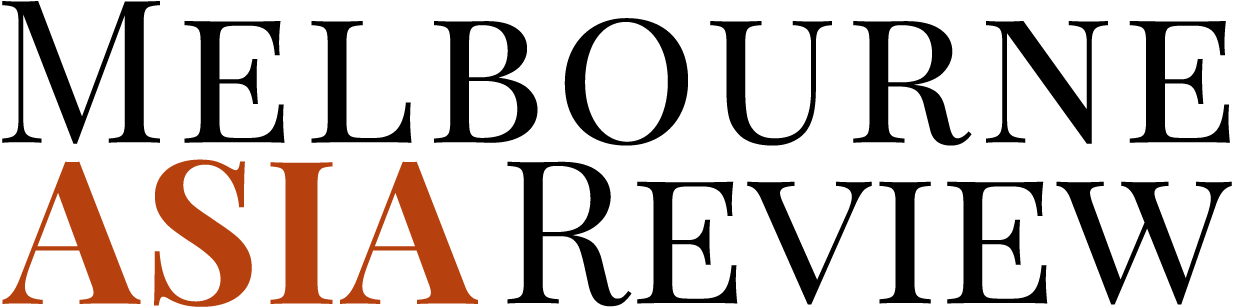译者:杨晨 尹雅萱 于博洋 张祎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构想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应试者的理念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在2018年的一次演讲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党比作考生。中国人民将会是这份试卷的评分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党经常强调“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
这个比喻突出了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文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习近平的比喻借鉴了最近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相应的这个比喻又参考了毛泽东在1949年3月即将在北京夺取政权时把中国共产党比作一个踏上赶考之路的人。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以考试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体系崩塌的背景下,所以这些比喻就有着很深的讽刺意味,即便是共产党党内人士也对传统教育体系遗留的问题进行了彻底批判。
2021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并执政60多年后,考试及其意义和社会意义仍然是中国政治争论的核心问题。大学入学考试在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教育体系曲折的试验阶段)被废除后,在1977年又得以恢复。在这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社会似乎对考试的价值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但最近政府禁止繁重的家庭作业和限制私人辅导机构的政策,也可以看作是对应试教育体制的负面影响持续感到担忧的表现。我们认为,这种担忧与人们对应试型教育的社会影响的担忧相呼应,它在中国社会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帝国时期。
2021年7月底,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一份联合文件提出减少义务教育阶段(即小学和初中阶段教育)学生和家长负担的措施之后,中国教育部发布了一系列新规定,目的是减少家庭作业,限制营利性课后辅导活动。如今,这类公司被禁止提供学校核心课程的辅导,这些公司也被禁止融资。现在小学老师和中学教师也被禁止从课外辅导中获利。
许多评论家指出,这些政策对当时蓬勃发展的课外辅导行业造成了冲击,该行业的价值超过了1000亿美元。有些人认为,收紧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党内整风行动的措施,同时,这些政策也是考虑到降低家长的经济成本。因为出生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这种政策也能刺激出生率的提高。也有人认为,此举与最近对其他持续发展的私营经济领域(如信息技术)的干预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评论家们为这种行动是习近平时代中共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控制和指挥的典型。还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些减轻教育负担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形式,不会有什么实际影响。
到底发生了什么?官方说法和其他解读
虽然外国评论员对这些改革的关注集中在关闭私人辅导机构的问题上,但中国官方政策声明和中国媒体公开批准该政策的评论都强调了必须对学生的作业量进行限制。
这些评论有三个关注点: 最受关注的是学生福祉; 另外希望减轻教师的压力和缓解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担忧,这些关注点是造成学校系统压力的原因。
这些问题出现于一个共同背景之下,即教育系统是否应该主要以竞争性考试为导向,还是应该侧重于培养学生个人和集体的道德、文化和思想“素质”,“素质”指 “修养水平”或“性格品质,行为品质”。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提高人口素质的想法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言论的主要内容(尽管可以说其有更深的历史渊源)。
众所周知,在东亚国家,以考试为中心的高中和大学入学教育给学生带来了巨大压力。长期以来,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中小学教育以在校时间长、家庭作业多和对课外辅导,特别是私人教学机构的严重依赖为特点。就这一点来说,中国目前的情况与20世纪50年代后普遍出现在东亚非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现象如出一辙。事实上,全斗焕任职时的韩国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就禁止过私人辅导机构,直到90年代这一禁令才取消。中国与它实施这一禁令的根本原因相似,即私人辅导学校作为一种商业机构不符合道德标准且增加了学生的压力。
观察家这些东亚国家的学生所承受的压力归咎于“儒家”的价值理念,或者是国家主导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发展计划,因为这些国家的教育体制在塑造现代公民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同时,正规学历证书对确立社会地位至关重要,这也加剧了学校体系内激烈的竞争。像在中国、韩国和日本这样的现代东亚社会中,(通过考试)进入精英大学是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志。
当然,在大多数现代工业社会中,为了上顶尖大学所面临的竞争对教育实践有巨大影响。在东亚,特别是中国,最突出的影响因素就是当前竞争性教育制度产生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如上所述,限制家庭作业量和禁止私人辅导是以中国现行的指导计划为框架的尝试,该计划旨在通过提高公民的道德、文化和思想素质的教育来弥补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但迄今为止基本上都失败了。
中国评论家认为,过度关注考试会导致学生缺乏体育锻炼从而身体虚弱或体重超标。 同样,有人认为家庭作业和课后辅导给学生带来了巨大负担,使他们无法参加学校规定课程之外的活动。这些活动在考试范畴之外,例如发展艺术和工艺方面的能力以及获得有关自然世界的知识。对于习惯于谈论传授正规学科知识和 “全人教育”对重要性的人来说,他们十分熟悉这些问题;在许多不同教育文化中,通过教育充分发展人的智力、文化和社会能力是其共同的愿望 。和东亚国家一样,受过高等教育却无法适应现实世界的 “书呆子 ”或 “极客 ”在欧美也是令社会焦虑的对象。
中国的考试,教育,权力:长远历史
在中国现代社会,人们对教育未能实现其目标的担忧比对教育体系的长期不满更能说明教育在社会和政治秩序中所起的作用的不确定性。研究东亚和东南亚历史的学者指出,在始于17、18世纪的社会动荡时期,教育问题在质疑当时的秩序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研究中国及越南的史学家亚历山大·伍德赛德 (Alexander Woodside)指出,通过考试选拔政府官员的传统制度是东亚社会教育乌托邦主义的重要文化遗产。
他认为,根据考试成绩选出高级官员的方式,不仅仅创造了一种以取得考试成功为导向、看似合乎情理并具有官僚性质的教育方式,而且还促使这些学生将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与他们在古籍中看到的理想教育做对比,进而产生异议。
这种异议模式将学校教育置于理想的人类社会组织的中心,并将古代学校教育的理想化愿景应用于对当今考试文化的批评。他还表明,在中国封建王朝后几个世纪,即在中国知识分子与欧洲世界深入交流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往往通过重建被认为存在于封建周朝至孔子时代(约公元前8-5世纪)的理想教育世界来表达对既定秩序的不满以及对改革的呼吁。伍德赛德表示,“当知识分子的呼吁作为一个异化和潜在救赎的寓言发挥作用时,这个有关封建教育的黄金时代的梦想可以说是中国版的阿卡迪亚传说,甚至等同于同一时期欧洲思想中的高贵野蛮人,尽管它的原始主义色彩较少”。
虽然中华封建帝国晚期的乌托邦主义关于教育这一部分早已淡化,但教育对社会和政治带来的价值的关注,以及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弊端的焦虑,甚至在1905年科举考试废除后,依旧延续并转变成文化关注的焦点。事实上,19世纪90年代(如果不是更早之前)出现的教育制度危机是推翻清朝前后期1911年爆发革命并重塑中国的一个主要因素。
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从某种程度体现了这一时期以教育为重点的激进主义。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记述关于毛泽东的童年和青年时写到,他投射的失望感得到了许多人的共鸣,因为这些人早期的学校教育侧重于中国经典典籍,而这种教育体系也被认定为不能满足当时的时代需求。这种失望感让他开始寻求彻底的教育变革。伍德赛德关于中华帝国晚期教育乌托邦式传统的评论让我们对毛泽东激进式教育有了进一步了解,其并非已经到了传统教育被西方新世界的科学技术知识所取代的绝境。
中华封建帝国晚期和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共同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公共和私人模式在教育中的作用。
虽然传统考试制度是一个公共的、国家组织的事务,但在帝国封建时代后期,这种制度的学校教育一般都掌握在私塾和学堂手中。
对教育理想主义者来说,他们幻想一个改革后的学校教育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平民也有机会获得道德教育的机会。而现实是登科及第才能获得国家发放俸禄的官职,再加上私塾的设立,这些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脱节,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在不受监管、唯利是图的环境下,经典书籍中所传达的传统道德思想怎么能够保留下来,更别说应用到现实中了。这种担忧,尽管与当下中国的教育计划毫无关系,但却从近期打压私人辅导这件事中略窥一斑。
随着1911年帝国制度被推翻,这些遗留问题开始与学校教育和建立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相融合。若培养公民建设新中华民国,则需要一个全面的国民教育体系。
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内容方针几乎无法达成一致,包括在新的学校系统中教授什么,甚至在如何创建教学系统方面都分歧颇大。
传教士开办的西式学校、各种遵循传统的旧式学校、新的军事院校和商业学校,以及革命党的宣传性教育实践举措在中华民国时期(1911-49年)相互竞争,但都没有取得最终胜利。
这些问题在中国的农村尤为突出。由于教师所在学校和岗位和缺乏资金来源,所以偏远地区的农村教师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成为中国共产党招募人才的主要目标人群,而在1927年后,中国共产党被迫离开城市,开始将自己重新定义为一个在农民中倡导革命的政党。
所以说,推动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进行土地再分配政策的一个因素是他们相信农村公办学校最终会为党所用。就像它是一个对经济进行革命改造的政党一样,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教育革命的政党。
社会主义将带来一种新的教育秩序,它将推动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彻底变革,同时带来一种新型的教育:一种既能替代中国传统教育结构又能替代资本主义国家教育模式的教育。
正如社会学家乔尔·安德烈亚斯所说,当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上台时,其对两方面感到不满:一个是旧教育体制,另外一个是在这种体制帮助下构建形成的社会。
然而,建国后的革命运动一直受社会主义文化之前遗留的问题的影响,尤其是1949年前的教育体制。
在毛泽东领导的前几十年里,以彻底重建教育体制为目标和继续依赖旧的学校教育两种模式之间一直存在矛盾,特别是靠考试来培养下一代的模式。这些矛盾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如上所述,当时所有考试都面临取消。
教育与平等
读过安德烈亚斯作品的人也许会注意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在接下来的50年里,已经从一个史无前例、大规模的社会平等运动的先行者在21世纪初变成了一个以高度不平等和互相竞争为特征的社会,这种竞争尤其体现在教育方面。
同时,当前中国的领导阶级的权力相对集中,凌驾于中国其他阶层的权力之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与其排外性质的教育体制有关,该体制剥夺了处于精英圈层外群体挑战统治秩序的资源。
对于非精英阶层来说,大学入学考试给这些寻求提高社会地位的人带来了无数的阻碍和困难。如果说有一件事情能够同时体现精英和非精英阶层的不满,那就是教育了。特别是选拔性考试带来的影响,不论是具有支配权的群体,还是被支配的群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
目前中国的一些执政者,包括习近平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后的几年里都接受了至关重要的教育,当时社会平等的政治口号虽然没有得到实践,但也相当激进,其中就包括对以考试为基础的教育性评估的强烈批评。
在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虽然这种对考试的批判在邓小平发起的改革中被果断否绝,但其中的一些理念持续影响着对教育的思考。党内高层人士(包括习近平本人)面临的一个新难题是,他们的孩子在考试中要接受匿名评估,这也就意味着其孩子可能无法进入一些中国顶尖的大学。
因考试性原则能够确保公正性,所以广受公众支持,但对一些精英家庭来说,他们的孩子可能会输掉与非精英家庭孩子的竞争,这导致他们要求能够根据考试分数以外的因素来进行评估。此外,人们认为目前的教育体制没有提供足够的空间来发展领导阶级再生产所需的领导技能。
自从禁止私人辅导和限制家庭作业量以来,中国媒体中出现的许多评论都集中在学校学生的“道德、审美、社会和身体”能力的发展上,这些都与培养学生的社会领导力有关。
禁止私人辅导和限制家庭作业的这些政策,是中国试图干预日益复杂的教育环境的一些尝试,其不仅包括对以顶尖公立大学、学校为主的旧教育经济的干预,还有对新兴的私立学校、国际学校、私营职业培训中心、慈善教育、文化机构和全球化教育“市场”的干预。
对一些人来说,禁止私人补习代表了中国对“谁教”和“教什么”的重新管控。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使过度严厉的学校教育制度人性化和柔软化的一种尝试,这种学校教育制度挑战了学生的极限,并迫使父母在学校之外为孩子寻找教育机会。但是,正如我们所论证的,这些禁令或许也呼应了一个古老的教育理想主义传统,它以社会主义甚至社会主义以前的教育理念为基础,强调对人和社会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改造。
正如亚历山大·伍德赛德所言,这种现代性不仅仅是与17、18、19世纪在环大西洋国家出现的工业结构碰撞的历史产物,甚至可以说是,最终成为了早在10、11世纪就在中国出现的以考试为中心的“后封建”社会和文化秩序发展的一部分。
自20世纪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在以考试为中心并由教育决定命运的社会中出现了特有的现代焦虑,因此,这在当代中国并不新鲜。伍德赛德观察到,中国长期以来以教育为条件的政治,产生了一种社会和政治冲突蔓延到教育领域的趋势,就像“现代美国政治的宪政性质不断地威胁着基本政治活动,其可能很容易演变为惊动法院的案例”。
我们认为,中国最近加强了对私人辅导和家庭作业的管控,这是教育与现代化之间复杂关系的一个体现,这种复杂关系尤指竞争性考试制度的体验。
人们渴望量化考试成绩予以公正评估,同时,也感知到这种量化考试所导致的社会与更深层次、更有意义的人类发展相背离的感知,这两者之间矛盾;这种矛盾在当今中国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它也存在于其他任何一个面临现代性结构和经验所导致的问题的地方。
Authors: Dr Lewis Mayo, Asia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nd Dr Justin Tighe, Trinity Colleg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Image credit: Rex Pe/Flickr.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on October 17,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