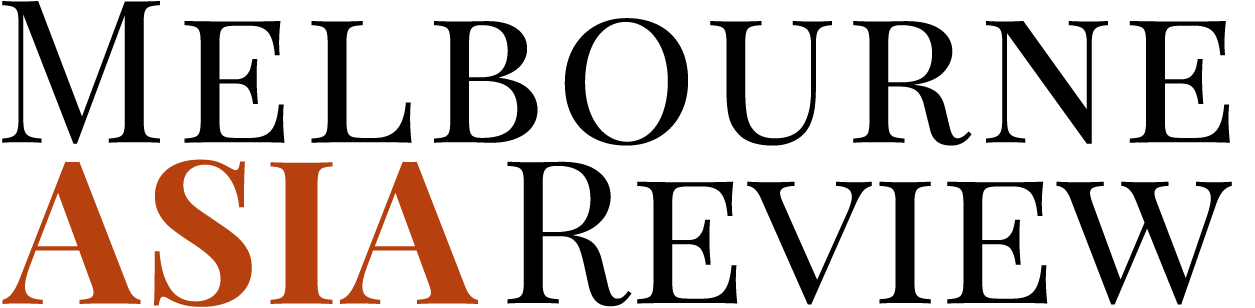译者:程佳惠、李一苇、林筠晴、林心诺、刘美池、赵东飞
中国俗语有云“谈性色变” (指人们一谈到性,脸色就变得苍白),虽然听上去有些过时,但在当今许多情况下仍然适用。很多层面上来说,中文中对性的谈论仍受到社会、文化和道德规范的约束。
尽管每种语言都存在此类限制,但中文在儒家思想和人们的道德观念影响下,与英语大相径庭。
儒学典籍中记载的“性”
作为一个哲学术语,汉字“性“可以译为英文中的“nature”(本性)——人和其他物种的本性得到广泛讨论,正如英语语境下讨论事物的本质。然而,性这一概念在儒家思想和其他思想中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后,“性”才翻译成了 “sex”。
中国语言学家傅斯年和威尔士汉学家葛瑞汉 (Angus Charles Graham) 研究发现,在中国秦汉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性”字和“生”字往往一起使用。这些文学作品大概是目前能够找到有关“性”含义最早的资料记载。许多情况下,比如在词语“养性”中,“性”字可能指 “生命”,具体指健康、幸福和长寿。中国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记载了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68年的历史,书中提及的“性”字有人类兴旺之意。比如,“勿使失性”一词,意为不要让百姓丢掉生计。此外,《左传》中的“性”字也指产生于天地之间、人体之内的“气”,表示能量: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1]
因此,人们通常认为“性”与生命力有关。
公元前四世纪,“性”字仍然与健康和人们对长寿的渴望有关,其中一个例子是“水之性”,表示只有当精神是自由且自然的,精神才是无瑕的。
儒学主导的历史中,仍然保有对人性善恶的区分,对塑造现、当代汉语中的“性”也有所影响。在中国哲学家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的语录中曾提到 “有性善,有性不善”[2] 。这自然会使母语为英语的读者想起 “good natured” (好的本性) 和 “bad-natured”(坏的本性)这两个词。
“食色,性也”可以说是我们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能找到的最好的例子,用以探究“性”与“sex”之间关系,这个表达最早出现在中国哲学家告子(公元前420年—公元前350年)撰写的《孟子·告子上》一书中: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內也。」[3]
然而,学者冯珠娣(Judith Farquhar)并不赞同刘殿爵(D.C. Lau)对上述句子的英文翻译,在她看来:“刘是在信口开河, 并且先入为主地认为人类天生对食物和性有着强烈欲望。”告子将人类对食物或性的渴望,视作身体真实体验和感受的信号。脱离语境,“食色性也”一词体现了对于人的天性、自我放纵等普世常识的理解。
儒学经典著作中,“性”的概念包含人体和人类生活的其他必需要素间的关系,比如对性和食物的渴望,更重要的是如何衡量和判断这些必需要素。人类的天性是渴望获得健康、长寿、性和食物,而非共同的利益。这也就是儒家理论下的“性”。
近现代中国“性”字的性化
在20世纪初期,中国经历了数次巨大的社会变革,例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项运动倡导学习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主张摒弃传统的儒家的思想、伦理和哲学。部分中国人似乎渴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现代化,并“追赶”西方的步伐。历史学家马修·哈维·索默(Matthew Harvey Sommer)指出,西方国家在此期间“已经极大程度上给予个人在性、婚姻和生育等方面的选择自由。”
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引进并翻译了许多有关性学和性教育的文章。有关性、性机制[4]的新术语与言论大量涌现,随即出现了一种人体健康、新兴医学和精神病理学视角下的性观点。例如, 叶德辉著写的《双梅景暗丛书》、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编写、中国社会学家和优生学家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学生手册》(Psychology of Sex: A Manual for Students)。在有关婚姻、生育和性卫生的手册中,能够明显观察到对性的认识已从传统形而上学转变到西方科学视角。许多人使用诸如交合、生育力和生殖器之类的术语来代替性本身,例如《生殖器新书》和《戒淫养生男女种子交合新论》[5] 。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汉语“性”的概念是从日语引入的,而日语中性的概念又是从英语词汇“sex”翻译而来:有证据表明,日语用日本汉字“性”来翻译“sex”(性)和“sexuality”(性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中国“性”的概念一定与西方性学及其对性的理解具有完全一致的定义和内涵。因为当概念从源语译入目的语时,其含义更多地是在目的语本土环境中得到“重塑”而不是“转化”。因此,“性”成为一个新词;在重新定义后,性的概念用以表示性道德。
后毛泽东时代下的“性”
中国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后,长久以来本由儒家思想定义的性道德,借由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重新定义。在英语、俄语和日语等语言的翻译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构想了与性道德相关的中文表述,但对性行为的道德约束并未明显放松。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将一种新的道德观念投射到性及其相关的语言、商品和行为上。进入新中国時期后,持续影响“性”相关的词语在语言学层面上的发展。
无论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在主流学术界,“性”(性别和性欲)相关的表达总带着边缘化和道德评判的意味。例如,在著名社会学家、性学家李银河的著作中,她用“亚文化”一词来标识同性恋,并称其为“虐恋”;在1998年发表的《同性恋亚文化》和《虐恋亚文化》两本著作中,她将同性恋视为一种性活动,与捆绑、束缚、支配、臣服和性虐待分为一类。将同性恋归类为一种亚文化,并将其与性虐待在某种程度上视为等同,因此边缘化了同性恋爱关系和酷儿[6]生活方式。
当今中国,多元群体和社会团体在线上线下蓬勃发展,各类词语直接从英文借用(而非使用中文翻译),例如“ bi”(双性恋/双性同体),“ les”(女同性恋者),“ fuck”,“ gay”,“ G”( 表示“男同性恋者”)。 然而,围绕性的论述仍然与性道德联系在一起,日常用语中大量关于性的术语仍体现了传统的道德警示和评判。中文里“性变态”、“性倒错”、“淫乱”仍指向性活动和性身份,譬如同性恋、异装、变性、性施虐者、性受虐者,虐待狂和恋物癖的人。
当今对“性”的重新定义、翻译和现代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字“性”经历了创造、翻译和重译的过程,具有多变的用法和丰富的含义。
儒学对于“性”的描述是建立在人性本能的前提上,然而现代性道德的论述往往与現代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价值观念密不可分。 这表明一个“译后的”现代性受到压抑、异化和边缘化,并且亟待重新翻译、重新构想和重新理解。作为一种不断吸纳新词汇、创造新短语、 丰富语言表达的语言,中文将在不同時期不同语境內继续探索“性”和(或)“sex”的重新翻译、重新想象和重新解读。
图片:在艺术北京2015的活动上,一位女士正在给一张绘有裸体女性的画作拍照。作者摄于2015年4月30日
[1] 英国著名气象和天文学家詹姆斯·莱格(James Legge) 曾经把这句古文翻译成“Modelling ourselves on the luminaries of heaven, basing ourselves on the life-cycles [xing] of earth, we generate their six energies and utilise their five elements”。 —译者注
[2] “有性善,有性不善”出自《孟子告子上》一书,意指有的人天性是善良的,有的则不是。—译者注
[3] 香港语言学家及翻译家刘殿爵(D.C. Lau)在翻译《孟子》英文版時把这句古文翻译成 “Gao said: Appetite for food and sex is nature. Benevolence is internal, not external; righteousness is external, not internal.” —译者注
[4] Sexuality在学术界存在多种翻译,如在福柯撰写的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一书中,书名被译为《性经验史》,在《纪大伟读同志文学史》一文中,将sexuality译为“性机制”。
[5] 《戒淫养生男女种子交合新论》由美国作家法乌罗和日本作家神田彦太郎合著,于1901年在中囯出版。该书提及有关性禁欲,健康养生和受精的新理论。—译者注
[6] “酷儿” 来自英文“Queer”,意指「古怪的,与平常不同的」。“酷儿”在1980年开始在同志圈中普及,强调个人性别身份及欲望的流动与多元,以及与异性恋不同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译者注
作者特别感谢Delia Lin博士和史峻(Craig A Smith)博士的慷慨支持以及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
中译文较原文略作改动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has been slightly modified from the original and has been modified slightly since i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mage: A woman taking photos of a painting that depicts a nude female body at Art Beijing 2015. Photographed 30 April 2015 by the auth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