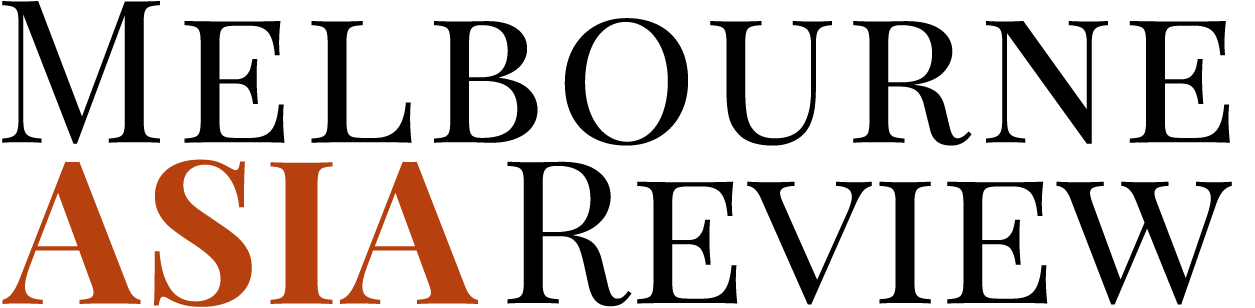译者:程佳惠、李一苇、林筠晴、林心诺、刘美池、赵东飞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大量证据表明澳大利亚的恐华情绪高涨,同时反亚裔种族主义现象激增。
种族主义浪潮再次抬头虽然令人担忧,但也并不意外。回顾澳洲历史,种族歧视现象屡见不鲜。从十九世纪中后期“淘金热”时的中国移民,到二十世纪早期和中期的亚洲移民,以及“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的穆斯林群体,澳大利亚的多个移民群体,尤其是亚裔移民,都曾遭遇过种族歧视。
澳大利亚反移民的种族主义的反复出现,表明种族歧视一直未被根除。要终结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除了疾声谴责之外,我们需要更系统地分析澳大利亚种族主义问题存在的根源。
新冠疫情下反华、反亚裔情绪再次抬头
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反华以及反亚裔的种族主义现象频繁在澳大利亚多地发生。
根据斯坎伦基金会(Scanlon Foundation)的一份重要报告显示,近六成澳大利亚华人以及亚裔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种族主义是一个“非常严重”或“相当严重”的问题。在近期的一份样本量为3000人的调查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近85%的亚裔澳大利亚人都表示自己在疫情期间遭受过种族歧视。然而事实上,在2020年4月份(澳大利亚发现首例新冠肺炎后的第三个月),澳大利亚只有极小比例的病例(0.35%)来自中国大陆,绝大部分来自欧美国家。如澳大利亚亚裔联盟召集人庄东升(Thomson Ch’ng)所言,“新冠疫情无疑滋长了澳大利亚社会长期以来的毒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澳大利亚部分媒体使情况升级,一些无良媒体助长了针对亚裔,尤其是中国移民的种族主义的气焰。相关研究对澳洲媒体报道的分析显示,华人已经成为众多澳州种族主义舆论文章的攻击对象。在与华人相关的报道中,过半数(55%)新闻评论都是负面的。
反华和反亚裔的种族主义在澳大利亚由来已久。历史上,19世纪中期开始,受淘金热的影响,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吸引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其中,以华人为代表的亚洲淘金者被广泛视作“黄祸[1]”(yellow peril)。在排华情绪的影响下,20世纪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后,议会通过的首批立法之一就是《移民限制法令》,限制包括华人在内的非欧洲移民入境。这一后来被广泛称作“白澳政策”的法令由此被确立为澳大利亚的基本国策,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正式在法律层面被废止。
亚裔鲜少担任领导角色,公共形象多遭扭曲
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不仅仅是态度上的歧视以及语言或者身体攻击。边缘化和异化也是亟待解决的显著问题。
有学者指出,澳大利亚拥有一个“欧亚未来”。在人口层面,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的人口结构经历了一个缓慢却显著的亚洲化过程,。虽然澳大利亚的移民仍主要自于英国和新西兰,但是澳大利亚海外出生的居民中, 出生在中国及印度人数的比例自2012年起呈上升趋势(分别从6%上升到8.3%,5.6%上升到7.4%)。
但是,亚裔群体的人口比例并没有直接转化为社会影响力。亚裔在澳大利亚社会和政治中鲜少担任关键领导角色,仍处于边缘地位。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澳大利亚的组织(包括商业、政治、政府和高等教育)中,95%的高层领导人都有盎格鲁-凯尔特[2]或欧洲背景。高层中有亚裔背景的只占3.1%,与其形成鲜明对比。
除了社会影响力的缺失,公共形象的扭曲也是亚裔所面临的一大问题。近年来,澳洲媒体常将华裔与“中国威胁论”相联系。任何被视作与中国政府或者共产党有联系的具有华裔背景的政界人士和社区领袖都很难免受到质疑,甚至被指控参与了中国对澳的政治干预。华裔自由党议员廖婵娥(Gladys Liu)在2019年联邦大选中赢得墨尔本东部奇泽姆(Chisholm)选区席位之后,长期被指与中国政府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导致“其议会席位资格受到质疑”。
对于华裔澳大利亚政治家、候选人,甚至是普通社区成员来说,一旦活跃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他们作为合法的澳大利亚政治参与者的身份就会难免受到质疑。这对于试图跻身澳大利亚政坛的华裔人士来说,“华裔背景(中国性)”似乎成了一柄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他们的政治生涯。
澳大利亚对于亚洲化的焦虑由来已久
究其根源,澳大利亚的反亚裔种族主义与其对亚洲化根深蒂固的焦虑密切相关。
客观上,亚洲化已经成为澳大利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这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移民以及澳大利亚和亚洲的经济联系加深所推动。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霍克-基廷政府(Hawke-Keating government)[3]就提出澳大利亚拥有亚洲未来。2012年《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白皮书呼吁,为了澳大利亚在21世纪的繁荣发展,澳大利亚应与亚洲加强互动。经济上,澳大利亚确实已在经济层面对亚洲产生依赖:2017年至2018年,与亚洲的贸易量占澳大利亚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量的近三分之二;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有12个是亚洲国家,中国是其最大贸易伙伴。
然而,情感上,澳大利亚仍未做好准备接受“亚洲未来”的理念和亚洲化的现实。澳大利亚在从根本上仍认为自己是一个西方国家。因此,对自身远离欧洲,地广人稀,但地处亚太,邻国人口稠密,深感焦虑。这种文化心理和地理位置,身份认知和未来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澳大利亚对亚洲化的抗拒心理。
澳大利亚政治家宝琳·汉森(Pauline Hanson)相当明确地表达出对于“亚洲化”的忧虑。她在1996年首次向议会发表演说时即宣称澳大利亚可能“被亚洲人淹没”。眼见汉森政治声望不断提高,当时由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领导的联邦政府再次肯定了澳大利亚的欧洲文化、历史传承,称其为“传承欧洲,联结北美,地处亚太”的国家。
撇开焦虑不谈,澳大利亚人在面对亚裔时,在心理和态度上都一直抱有优越感,始终将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亚洲移民视为 “外人”。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针对原住民和非欧洲人种的种族歧视根源在于澳大利亚自殖民时期延续至今的白人优越感和特权感。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一直自认为在许多方面比其亚洲邻国更加优越,这也是为外界广泛接受。诚然,澳大利亚先于许多亚洲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和福利国家,但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发展上越来越依赖亚洲国家也是不争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澳大利亚的优越感源于在澳大利亚成为 “亚洲的采石场”之前,其社会经济对亚洲邻国的优势,以及对亚洲 “贫穷、落后、不稳定”的成见。
因而,正如洪美恩(Ien Ang)教授指出,澳大利亚面对经济上被亚洲邻国超越、经济繁荣依赖于非西方的亚洲国家这一事实,心态上很难理解和接受。经济层面对正在崛起的亚洲的依赖,尤其是对中国的依赖,往往会加剧而非缓解澳大利亚对于“亚洲化”的焦虑和恐惧。
加剧种族主义:媒体贩卖恐惧
澳大利亚有影响力的部分媒体在转播和助长种族主义上充当了重要角色。市场竞争激烈,政府补贴缺乏,澳大利亚媒体普遍面临财政困境,其竞争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博取消费者的关注。此外,媒体所有权由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等少数公司集中掌握。在此背景之下,相比于细致的事实核查,制造出博人眼球的报道对于媒体来说更加有利可图。因而,中国或者是澳洲华人(包括留学生)如何对澳洲安全构成威胁这类报道常见报端。
媒体报道中,移民为社会问题背锅并不新奇。近年来,媒体将一系列问题归咎于中国移民,比如房价上涨、外来政治干涉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除华人移民之外,媒体的报道中也将穆斯林群体与恐怖主义、非洲裔与街头帮派混为一谈。
这类报道之所层出不穷,是因为利用了澳大利亚国民对社会不平等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的担忧。这种担忧无关种族背景和移民身份,为所有澳大利亚人所共有。致力于使澳大利亚变得平等和安全无疑极其重要,然而,严谨公正地报道或探讨与移民有关的社会问题并呼吁认真解决是一回事,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将这些问题简单粗暴地归咎于移民又是另一回事。前者将有助于澳大利亚认识到移民对澳大利亚发展的潜力,而后者则会制造和加剧与移民有关的焦虑,助长种族主义。
建立和维持社会经济平等和国家安全体系需要深入分析问题和积极灵活地应对问题。让移民群体为深刻和复杂的社会问题背锅并不能使澳大利亚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更加安全。而且对于澳大利亚的少数族裔群体而言,这只会使澳大利亚更不公平、更加危险。
将亚洲性纳入澳大利亚国民身份认同
作为传统移民国家,澳大利亚对移民群体的人力和财力资本“胃口大开”,但是澳大利亚反移民种族主义的反复出现表明,澳大利亚在移民问题上仍存在 “消化不良”的问题:移民来到澳洲,建设澳洲,却仍未被完全接纳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当诸如失业、犯罪以及近期爆发的新冠疫情等结构性问题出现的时候,移民仍首当其冲,成为替罪羊。诚然,所谓的移民”消化不良”问题,并非澳大利亚所独有。但这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这个拥有悠久移民历史的国家没有责任或没有能力做得更好。
澳大利亚前反种族歧视专员蒂姆·索夫马赛博士(Dr. Tim Soutphommasane)指出,澳大利亚与亚洲的交流和往来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澳大利亚应对文化多样性的能力”。香港大学文学院前院长雷金庆博士也指出,对在澳华人的不信任和疏远有可能浪费澳大利亚的 “侨民优势”。
因此,消除种族主义,不仅能够给予移民他们应当享有的公平待遇,同时也能帮助澳大利亚充分获得移民带来的发展和社会效益。
面对新冠疫情期间高涨的种族主义情绪,澳大利亚亟需新的反种族主义总体框架和反种族歧视运动。然而,除非澳大利亚将将亚洲性纳入其国民身份认同,真正将亚裔群体和移民接纳为澳大利亚社会的一份子,正视并接受“亚洲化”的趋势,否则在澳大利亚反亚裔种族主义不太可能彻底消失。
[1] 以5分制量表衡量,从1=“从不”到5=“总是”。
[1] 以5分制量表衡量,从1=“完全不信任”到5=“非常信任”。
潘秋萍 博士 深圳技术大学助理教授兼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荣誉研究员
图片: 澳大利亚国庆日,于墨尔本,2014年。版权所属:Chris Phutully/WikiCommons。
中译文较原文略作改动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has been slightly modified from the original)
[1] “黄祸论”认为中国等东方黄种民族的国家是威胁欧洲的祸害。–译者注
[2] 盎格鲁-凯尔特人指出生于大不列颠群岛或者祖先来自于大不列颠群岛的澳大利亚居民。–译者注
[3] 霍克–基廷政府(1983年3月11日-1996年3月11日)。该时期内共有两届澳大利亚工党组成的政府执政。1983年至1991年,鲍勃·霍克(Bob Hawke)担任总理,1991年至1996年,保罗·基廷(Paul Keating)担任总理,基廷(Keating)担任整个霍克政府的司库。在霍克-基廷政府时期,工党连续五次赢得联邦选举,这是迄今为止选举最成功的时期。此次长达13年的连续政府统治期间,让工党成为了联邦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