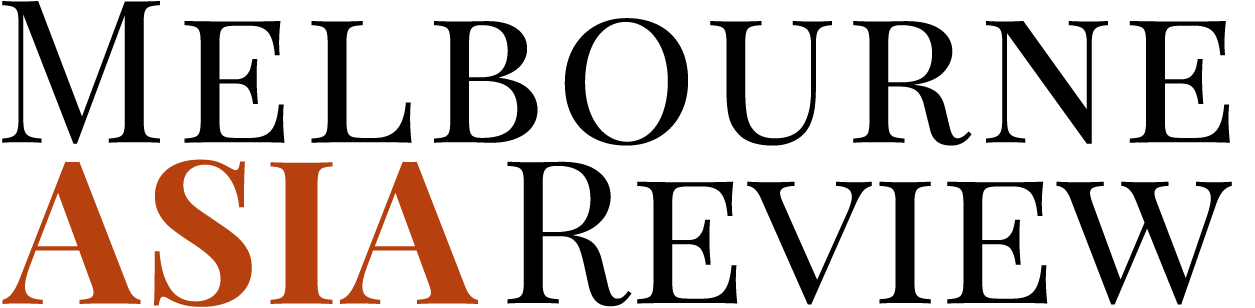譯者:葉穎蕎(Wing Kiu Yip)、朱沛翹(Pei Qiao Chu)
中國的平台經濟規模巨大且持續增長,消費者可以透過數碼平台預訂搭乘服務或餐飲外送服務。
這對缺乏就業保障的工人造成重大影響,他們往往在極大時間壓力下長時間工作,但只享有少許工作權利。
雖然這些問題不只局限於中國,但中國工人並不享有罷工權,結社自由不受法律保障,民間社會力量薄弱。
陳敬慈博士昔日為香港的勞工學者及社會運動參與者,現擔任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商學院高級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大陸及香港的勞工、公民社會和社會運動。他接受了《墨爾本亞洲評論》執行主編凱茜.哈珀(Cathy Harper)的採訪。
平台工作者,尤其是外賣食品速遞員,正在融入世界各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您可以大概描述一下這些工作者在中國的工作情況嗎?
現時大家都在談論數碼領域的零工化問題,中國也不例外。中國的不同之處在於,平台經濟工作者的佔比極高,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表明,2019年平台經濟工作者佔總勞動人口百分之9.7,遠高於英國的百分之4和美國的百分之0.4至0.6,2018年中國平台領域總共有7500萬名工作者,有關數字近年仍持續上升。
這些工作者有哪些主要特徵?
以主流外賣平台之一的美團為例,其百分之90的員工為男性,而且非常年輕,當中有百分之82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此外,百分之66的員工持有高中或以上學歷,百分之16的員工持有大專或大學學歷。在中國,工人來自農村或小城鎮十分常見,當中百分之85為農民工。
過去十多年來,中國政府推動了經濟升級戰略,部分工廠被關閉,並遷往越南和其他國家,以便政府更好地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但中國實則仍需要大量處於勞動等級低端的非技術工人。
為什麼來自農村的工人要做這些收入不高、工作條件不好的工作,尤其是當他們受過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
中國國內勞動力遷移歷史由來已久,自1978年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以來,源源不絕的勞動力從農村遷往城市,主要是廣州、深圳等華南地區,以及華東地區。現時這種勞動力遷移模式仍在持續,然而,追溯至毛澤東領導時期,中國自1958年開始實行戶籍制度,使這些工人無法在城市永久定居。這項政策把全國人口劃分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未經許可,居民不得遷移到國內其他地方定居。1978年後,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工人(在中國泛稱為「農民工」)被允許在城市工作,但他們所持有的仍然是農村戶口,這意味著他們無法享受城市工人的社會福利。
過去二十年來,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出現變化。例如,自2011年施行的《社會保險法》規定,包括城鎮職工和農民工在內,所有職工都有權享受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保險(俗稱五險)。另一項條例也規定,僱主應當為包括農民工在內的職工繳納住房公積金,這代表在工廠或公司工作的農民工有權享有「五險」和住房公積金保障。但關鍵在於,中國法律執行不力,因此農民工的社會保險參保率仍然很低。
農民工進城落戶的另一個障礙是城市的住房和生活成本遠高於農村。持有農村戶口的農民工依然可以住在自家的房子,以及在農地工作。如今有些城市能夠為農民工提供城市戶口,尤其是持有高等教育學歷的技術工人,但部分工人更傾向於保留農村戶口,因為擁有農村房屋及城市工作可以降低生活成本。這是農民工們普遍接受的安排,他們的家人往往留在農村生活,子女的教育費用和年邁父母的生活開支在農村要低得多。
平台工作者在工作過程中會遇到哪些問題?
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衰落,許多農民工目前在服務行業工作,包括發展蓬勃的平台經濟。關鍵的結構性問題是:平台工作者缺乏社會保險和勞動合約,他們被歸類為自僱人士,因此不受勞動法例保障。以外賣食品速遞行業為例,在2017年以前,有些工人是由平台根據勞動合約直接僱用,但在2018年之後,直接僱傭模式被外包模式取代,即工人不是由平台本身僱用,而是由人力資源服務機構視為獨立承包商僱用,這意味著工人失去了社會保險和其他就業保護的保障權利。而中國的特殊情況在於,外包制度可以分為多個層次: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可以進一步將業務承包給規模更小的公司,導致工人更加難以索償。
與全球各大巨頭公司相互競爭的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國內民營資本在其市場佔據主導地位。在外賣食品速遞領域有兩大巨頭,一是提供本地消費品和零售服務的購物平台 — 美團,另一個是提供外賣食品速遞服務的網上平台 — 餓了麼。兩大巨頭相互競爭,為客戶削減服務費,這意味著他們向工人支付更低工資。自2018年起,計件工資持續下降。這一問題衍生了許多抗議活動。人力資源服務機構聲稱,由於工人為獨立承包商,機構降低其計件工資並不需要事前與工人協商。對於工人來說,這是重大且緊迫的問題。
通常每天的工作時間和工資水平是多少?
工人分為兩類,一類是全職工人,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外賣食品速遞等零工,另一類是兼職工人。全職工人的工作時間通常較長,比如每天工作10小時或更長時間。與大城市的工廠工人相比,全職工人的工資不算太差,而且工作時間也有更大自由度。他們的總收入與工廠工人差不多,每月超過3000元人民幣,約合每月500美元。這是大城市的普遍收入水平,在二三線城市則較低。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採訪了一些工人,一位兼職工人告訴我們,他在經營自己的早餐店,早上賣早餐,在午餐時間送幾個小時外賣,晚上在餐廳打工。雖然平台工作者收入通常與工廠工人收入相近,但有些工人可以選擇不辭勞苦地工作,並通過延長工作時間賺取更多收入。
關鍵問題是,基於自僱人士的身份,平台工作者無權享受社會保險。例如,道路交通事故屢見不鮮,但平台工作者無法索取工傷補償,因為公司並沒有為他們投購工傷保險。另外,法律一般要求僱主按工資繳納較高比例予工人的養老保險。在部分城市,僱主必須繳納百分之18,工人則只需繳納百分之8,但實際上執行不力。由於零工工人被歸類為自僱人士,僱主不會為他們繳納養老保險。雖然收入可觀,但他們未能享有其他福利。
工人在抗議、罷工或其他形式的集體行動方面採取了哪些民間行動?
在中國,組織「野貓式」罷工(亦即「無組織」或半有組織的罷工)十分常見。這些活動是由非正式負責人組織,並非由工會組織。於2015年和2018年,國家對獨立的勞工非政府組織進行兩輪打壓。華南地區的一些勞工非政府組織早先在支持、組織工人抗議和集體行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2018年後便不再活躍。現時,大多數罷工皆由工人自行發起。2018年至2019年間,食品速遞行業出現大量工人抗議活動。正如我先前提及,2018年之前,外賣平台公司方才開業,為了穩定勞動力,公司為工人提供了更加優越的條件,包括正式僱傭合約。但2018年以後,隨著市場競爭加劇,工人的身份從直接僱員變為在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工作的獨立承包商。而且,正如我先前提及,企業不斷降低工人的計件服務費,這表示著工人若想維持收入水平,就必須更加努力工作。上述情況導致了許多抗議和罷工,數百名工人停工並試圖與公司(通常是下級公司、代理機構,而不是國家級母公司)進行談判。
你認為這些罷工行動有多成功?
作出讓步是外賣平台公司的慣常手法,但這偶爾與工人對就業保護和更高計件工資的核心擔憂並無直接關聯。計薪制度十分複雜:如果你在高峰時段工作,就可以獲得高於其他時段的薪水。還有工人個人績效評級制度:如果你的評級較高,就可以獲得更高工資或接訂單優先權。公司有時會在服務費計算方法、訂單分配方式或派發勤工獎獎金等問題上讓步。然而,公司少有直接對工人的核心擔憂 — 更高計件工資及包含社會保險的僱傭合約方面作出回應。
對於罷工參與者來說,他們可能會受到僱主的懲罰及/或被逮捕,這意味著什麼?
在中國,罷工權不受法律保障。但2002年至2012年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執政期間,地方政府接受了工人罷工的情況。甚至有學者認為,雖然1982年中國修改憲法取消了罷工權,但法律並沒有禁止罷工,因此這屬於中國法律體系中的「灰色地帶」。當時罷工非常普遍,而罷工參與者很少遭受處罰。但在習近平現任政府的領導下,過去十年推行用來鎮壓勞工抗議的限制性政策。罷工組織者時常遭到逮捕和監禁。
然而,「野貓式」罷工的規模可以很小,參與人數不到100人。在這些情況下,就很難識別出非正式負責人,而且罷工的影響有限,因此國家通常不會採取任何懲罰措施。但如果你試圖籌備一場規模更大、組織更具細的罷工,就會產生相應後果。較早前,我提到了2015年和2018年對非政府組織的打壓。這是因為當時一些非政府組織試圖組織工人罷工,或幫助工人在工作場所建立工會,這種籌備和組織方式不被中國共產黨允許。
盟主(「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工人陳國江組織了14000多名工人加入他創建的微信群組。然後他嘗試採取進一步行動,為聯盟參與者組織面對面會議。這種組織方法雖然屬於非正式性質,但在中國也屬於非常敏感的行動。陳國江於2021年初被捕,被控以罪名「尋釁滋事」。他被監禁12個月,出獄後一直保持沉默。這是處罰工人常見的模式:如果你僅僅參與罷工,可以接受;或如果你組織一次性、小規模的非正式罷工,那也不是什麼大問題。但如果行動變成高調運動,你就會被捕,外界也難以得知你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出於壓力,那些被捕的人在釋放後通常不會繼續行動。
習近平領導下的共產黨如何對鎮壓工人權利提出辯護?共產黨難道不是屬於工人的政黨嗎?
儘管中國因缺乏結社自由而受到批評,但他們說,工人可以建立工會,或成為工會成員。然而,所有工會都必須隸屬於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群眾團體之一,只有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地方分支機構才具有組織工會的合法權利。工人如果有意組織工會,必須先得到上級正式工會的批准和協助。官方工會並不支持或鼓勵罷工,因為這是非法的。過去,如果工人想要組織罷工,可以得到勞工非政府組織的支持,但自打壓以來,這些非政府組織被政府稱為「境外勢力」,這在政治層面而言對工人來說是危險的。
您認為中國平台工作者的就業情況如何反映中國民間社會情況?
過去有很多活躍的勞工非政府組織都是由國際基金會資助。此等勞工非政府組織由律師、記者、學者或工人自行創辦,是中國民間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領導下的國家對民間社會施壓,意味著勞工非政府組織如果想要生存,就必須改變策略。例如,勞工非政府組織只能從國家或經國家批准的基金會獲得資助,或者只能為工人提供勞動權利教育等服務。上述情況就是中國民間社會的整體狀況 — 這個專制國家對權力進行了進一步集中。
中國民間社會是否名存實亡,存在很大爭議。
另一方面,一些民間社會運動參與者亦表現出他們在勞工權利方面的韌性。記者或學生等社會運動參與者繼續發表有關勞工權利的文章,倡導政策變革。例如,北大一名研究生當了六個月的外賣食品速遞員,之後為大眾媒體撰寫學術論文和文章,在網上廣為流傳。隨後,主流媒體採訪了該名研究生,從而了解工作條件以及平台公司如何剝削工人。該名研究生成功引起了公眾對該議題的關注,這也是近年來政府加強保護平台工作者的原因之一。例如,政府於2021年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旨在保護平台工人的權利,當中包括最低工資和保險保障。
對於中國的民間社會運動參與者而言,這是非常困難的時期。西方語境中的民間社會強調組織的作用,而現時要在中國建立和維持獨立的組織卻十分困難。儘管如此,仍有許多人積極利用自身影響力改善政策,這些人或多或少地扮演著民間社會的角色。這是思考中國民間社會問題的另一種方式。
主圖片:一輛美團單車來源:喬恩·羅素(Jon Russell)/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