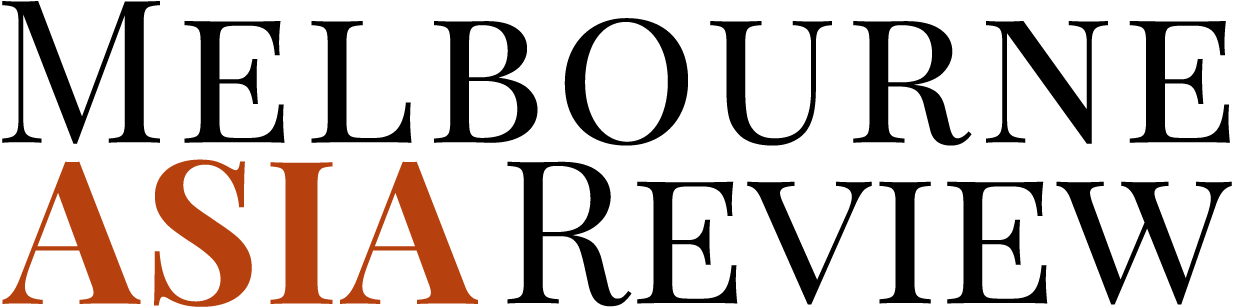译者:近来,受新冠疫情快速蔓延的影响,留学生面临危机,澳大利亚公立大学财务状况令人担忧。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体系面临的重重危机中,留学生生源流失是重要因素之一。
留学生带来的可观收入缩减,大学因此纷纷削减教职人员和课程。假设2021年留学生入学率下降20%,大学的收入损失预计将由33亿美元增至43亿美元。
相较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体系的危机,政府如何对待留学生更为重要。留学生群体并非政府留职津贴(JobKeeper)、求职津贴(JobSeeker)等多项津贴的援助对象,这就使得留学生的处境愈加绝望。政府此举精于算计,忽视留学生处境。多年来联邦政府和多数学校只将留学生视为摇钱树。
这场危机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政府漠视留学生福利的背后又是什么?
留学生对澳大利亚公立大学至关重要的原因:高等教育监管型国家的崛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任联邦工党政府教育部长的约翰·道金斯(John Dawkins)开始实施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使得澳大利亚开始并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监管型国家,走上管理公立大学之路。
监管治理是指发展监管型基础设施,通过使用行政规则、法规和标准,大学更具竞争力,并引导大学进入公立高等教育的市场体系。这些规则把控着资金的竞争性分配,即教育拨款和学生的助学贷款及补助金的分配,并使得监控机构绩效与质量的审计体系得以成立。
该监管体系结构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支持全额付费留学生的扩招。该监管框架包括《2000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案》,界定了保障留学生质量的监管标准。针对为留学生提供课程和学位的教育机构,该法案也设定了相关标准。在此框架下,监督和执行这些标准的工作,将由国家监管机构,即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管理局负责。
这些标准规定了留学生在澳就读期间及完成学业后工作的相关条件,这些条件与澳大利亚的移民和就业制度共同发挥效力,在尚未获得永久居留资格前,留学生因此成为了特殊的一类短期工。笔者将这些规章制度定义为高等教育监管型国家的国际化。
联邦政府不断削减对公立大学的经济支持,而留学生带来的收入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填补大学的经济空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已然将留学生的学费视为学校收入的主要来源,并通过高等教育管理机制对其进行管理和监督。另外,由于政府的经济支持力度弱,澳大利亚八大院校的科研组一直处于资金不足的状态,得益于商科等专业留学生学费的交叉补贴,学校的研究工作才得以维持。之后,在2020年联邦议会通过的高等教育改革中,教学和研究经费有效分离,科研集中型公立大学的经费将被进一步削减。
此外,在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和国家卫生和医学委员会等机构提供的研究补助金中,所有的间接支出仅有部分为政府拨款。因此,基础设施和仪器(如实验室和研究设备等)的经费都需另寻出处。而留学生学费便能填补这一空缺。
留学生既是学生又是在澳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是此次危机的根源
由于签证限制,留学生平日在两个星期内的工作时长不得超过40小时,放假期间则没有时长限制。据估计,超过40%的留学生在学习的同时需要有工作,其中印度学生占据主体。对于这些学生,没有工作就意味着失去收入,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在持续的疫情中,我们已目睹失去收入对留学生(特别是印度裔留学生)的影响之大。
作为监管型国家的产物,留学生的双重身份导致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薪资低、且遭受严苛待遇。新南威尔士大学和悉尼科技大学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据估计,许多留学生得到的薪水达不到最低薪资标准,更重要的是留学生并不会针对此情况进行投诉或采取行动。但在服务业或餐饮业,有学生反映存在霸凌和性骚扰现象。
简而言之,高等教育监管型国家的国际化滋生出就业乱象。要想全面了解目前的危机,我们需要设法理清制度规则同其社会经济影响间的关系。
毕业后的多种临时移民形式是成为永久居民的渠道
20世纪90年代末, 前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领导的政府首次提出了留学生毕业工作签证项目,由此教育和移民的联系便成为澳大利亚教育和移民体系的核心特征。从那时起,该项目的范围就从公立大学延伸至职业培训领域。
其最大影响是开创了一种新型临时移民形式,即留学生毕业后可凭借工作签证留在澳大利亚。先前的创新性研究记录了许多移民案例,指出持有临时签证是成功移民的关键。这种移民的“临时性”与在劳动力市场享受到的待遇和权利紧密相关。证据表明,持有临时移民签证、特别是从事护理和酒店服务业的群体,其薪资待遇并未达到特殊工种标准。这些研究将临时移民工作者(留学生)的不利处境和就业经历联系起来。此外,留学生的就业经历也清楚表明,临时移民获取政府援助或赔偿的权利和渠道都很有限。
种族主义制度化模式加深了留学生或移民工作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结构性弱势,这也是其无法享受诸如留职津贴(JobKeeper)、求职津贴(JobSeeker)等多项津贴的根源。丽莎·蒂利(Lisa Tilley)和罗比·希利安(Robbie Shilliam)两位学者近期提出“种族化市场”这一概念,可以作为分析种族和劳动力市场问题的有效理论框架。“种族化市场”旨在探讨种族差异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因此,制度化种族主义不能被简化为个人偏见、态度或信仰,而应被视为劳动力市场运作中的内在因素。
学者宋宪琳和格雷格·麦卡锡(Greg McCarthy)在其关于留学生的研究中,提及了种族化市场与留学生相关的概念。其主要观点是大学和政府机构对“文化差异”的构建是管理学生流动性的核心。笔者认为,这些“种族化市场”是深入了解留学生和其他临时移民者工作待遇的关键。正是由高等教育监管型国家机制下催生的(留学生)短期工身份,促成了种族化市场的运作。此概念强调了系统性种族主义模式是运作和管理核心服务业劳动力市场的关键。
由于相关政策的出台和个人选择,留学生陷入了就业和学习的灰色地带,这是教育和就业制度交叉的结果。它之所以很关键,是因为从广义上说,国际高等教育监管型国家出现已有三十年,它并不仅只是设立了一系列制度规则,其运作也间接地与劳动力市场相关联。在这样的劳动力市场中,留学生面临着危险的工作条件,就业的权利也非常有限,而这就需要从更宏大的背景去了解 ——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澳大利亚移民项目发生了改变,如今已有大量的移民持有各种类别的签证,包括毕业工作签证和澳大利亚居民合法身份。
为了应对当前危机所带来的巨大挑战,我们应确保留学生和其他短期工的权益都得到保护,不仅要保护学生身份所享有的权益,也要充分考虑短期工身份所享有的部分。
超越澳大利亚国界:留学生与区域政治经济
教育/移民监管型国家的影响超越了国界,与印度、中国等国的经济转型存在联系。
众多学生及其家庭为支付留学费用负债累累,而在印度情况尤甚。高额的留学费用为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越发沉重。如上文所述,留学生通常需要在学习期间同时工作来偿还留学产生的债务、并支付教育中介费用。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理解高等教育监管型国家如何推动并巩固债务与金融的跨国运作。学生/移民劳动力的独特混合形式是区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使得劳务市场出现多重身份的劳动力。这里的不平衡发展指的是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模式(包括工人与资本所有者和其他群体的关系)以及融入到全球经济中产生了收入和利润的不平衡,例如完全的出口导向型增长。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决定了留学生及其家庭如何支付留学产生的费用。例如,中国学生的留学费用有赖于中国的高储蓄率。这种高储蓄率是中国向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导致社会安全网受到破坏的产物。关键在于澳大利亚这一高等教育监管型国家结合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用一个政治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基础过程对国际教育部门的运作至关重要。
这种移民/教育监管关系的思路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它给不受保障的工作增加了条件,并将留学生排除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外,因为他们同时具有学生和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正是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这不仅仅是法律将其排除在外,更是一种政治上的抉择。
很显然,支撑着高等教育监管型国家国际化的深层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正在发生重大转变。这场新兴的危机有三个关键的因素:
- 中澳双边政治和经济关系紧张的加剧,可能导致两国间留学生流动量减少。
- 关于留学生在高校财政中作用的民粹主义论调愈演愈烈,使得情况很难回到新冠疫情爆发前的状态。同时,这使得政府更不可能支持或推动两国关系的恢复。联邦政府对留学生的故意漠视,导致民粹主义言论愈发激烈。政府正在对大学进行的重大财政和体制重组似乎忽视了支持和保护现有留学生的政策措施。
- 澳大利亚留学生扩招计划受到影响,例如,印度目前的经济困难会导致从该国扩大招收留学生的可能性降低。
图片:墨尔本的留学生 来源:阿尔法/弗里克(Alpha/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