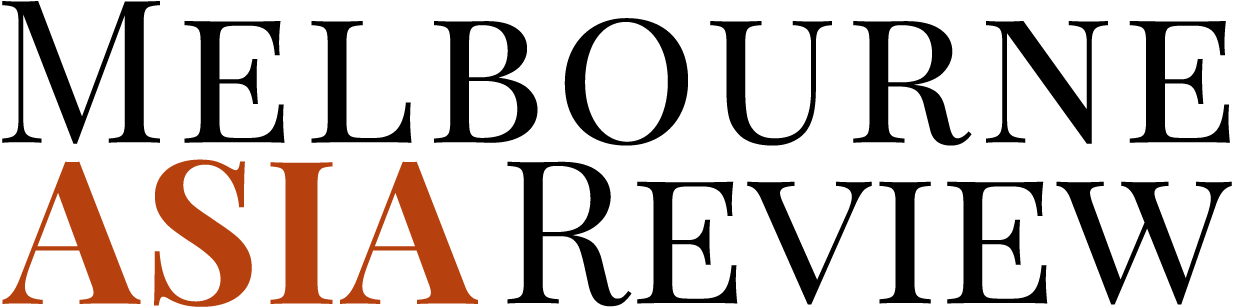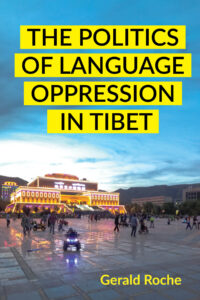
译者:杰森(Jason)、刘柯岑(Kelsey Liu)、李欣羲(Alison Li)
翻译审校:魏安天博士(Dr Anthony Williams)
语言流失问题并不只出现在世界上某些地方,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使其境内许多民族语言面临巨大威胁。中国的语言流失现象体现在语言(官方语言普通话除外)代际传承的中断。
《西藏语言压迫背后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Oppression in Tibet)一书为杰拉德·罗谢(Gerald Roche)撰写、近期出版的著作。该作品聚焦于来自西藏安多地区(Amdo)传统边界内同仁市(Rebgong)各村庄的马呢尕查语(Manegacha)使用者。马呢尕查语是西藏的众多少数语言之一,使用人数约为8000人。随着使用频率的下降,该语言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罗谢的著作对马呢尕查语使用者所面临的各种压力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马呢尕查语使用频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普通话进行推广的语言政策。政府在民族分类体系中承认了其他语言,并正式承认了56个指定的民族群体,其中包括藏族。每个民族群体都有一种指定的口语语言,而西藏的指定口语语言为藏语。然而,藏族人民使用着大约30种不同的语言,但按照民族分类体系的规定,“……在西藏地区中,只能推广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所谓假设的‘标准藏语’……这是藏族人唯一可以自由使用和发展的语言”(第47页)。因此,民族分类体系的影响是削弱了整个中国的语言多样性。
罗谢著作的优点和重要性在于,它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从复杂的跨学科视角分析了国家政策如何在推广某些语言的同时压制其他语言,从而限制个人和社群的语言选择空间。这本书聚焦于权力动态,并探讨了“……个人在其一生中对语言的选择,是如何被结构性因素所过度决定的……以及尝试分析说话者的主观能动性是如何被系统性地削弱、限制,甚至被剥夺的”(第6-7页),这些现状并非由全球化或现代化的推动因素所导致,而是那些掌权者的决策所致。为了展现这种对于主观能动性的削弱,罗谢在书中的引言部分以他观察到的一位藏族女孩与其父亲的对话为例。这位父亲在对话中解释了他和妻子虽然均为马呢尕查语使用者,却决定只用藏语与女儿交流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帮助女儿适应非马呢尕查语的学校教育。
在西藏,个人的语言选择不仅仅受国家级的限制,这正是西藏的境况尤其引人注目的地方。中国官方将西藏指定为自治区,其政府隶属于中国当局,而流亡藏人社群数十年来一直对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提出异议。
语言对藏人的重要性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包括以自焚的形式进行政治抗议——自2008年以来已有约160起。据报道,一位名叫才让杰(Tsering Gyal)的年轻僧人在自焚后表示,他希望“藏人能够保护并传承其语言和文化认同感”。
流亡藏人之间要能够相互沟通,因此藏语成为了实现这种交流的方式。罗谢指出:“民族主义鼓励藏人抛开差异,团结一致,弘扬和保护藏人的民族认同感。这意味着要将自己的藏人身份摆在首要位置,而非归属于某个特定地区、教派、社群或语言群体的一员。”(第65页)因此,对藏语作为单一共同语言的强调既带来负面影响,也有激励作用。
在论述这一点之后,罗谢便引入了“藏语圈”(“Tibetophonie”)的概念,指的是“……一个政治项目,旨在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藏人使用统一的藏语。”(第92页)这个术语不仅适用于西藏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濒危语言使用者群体,有助于对语言压迫进行更具体而细致的分析,且引发对语言“政治化”各种形式的思考。罗谢指出,通过强调统一的藏语,藏人却“默认了国家(即中国)的主张:藏人使用的唯一语言是统一的‘藏语’……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可以说全球藏语圈在话语上增强了国家的权力。”(第94页)藏语圈揭示了不同参与者在语言压迫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及其作用:即使藏语本身被边缘化,但它的优先地位却进一步边缘化了如马呢尕查语等其它语言。
罗谢运用福柯(Foucault)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概念来描述他所理解的权力弥散性和广泛性本质。“权力关系不仅是二元的、垂直的支配关系(压迫者及被压迫者间),还包括被压迫群体之间和群体内部的横向暴力关系,且涉及一定程度上的内化压迫。”(第12页)他并非主张是藏人有意或主动地让自身语言走向消亡,而是指出这种状况是中国所构建的生命政治国家体制的产物,也是流亡藏人所面临的困难和生活压力导致的结果。
尽管这本书聚焦于马呢尕查语使用者的案例,但对于语言压迫的未来研究,它仍提供了许多启示与考量。对于其他认为自身语言正在遭受威胁的少数群体来说,该书中的许多结论也同样适用。其中,许多群体正处于后殖民环境中,例如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他们曾拥有超过250种语言,还有这些语言的许多方言,而如今仅剩约120种。
《西藏语言压迫背后的政治》对马呢尕查语使用者及其持续的语言流失问题进行了详细而广泛的探讨。该书在结论部分向读者强调语言复兴项目的重要性,并以一种充满希望的语气收尾,强调政府与个体在语言复兴中的作用。罗谢在最后几页中传递的最为感人的信息之一是:“马呢尕查语或任何其他语言的消亡都并非不可避免,改变并非毫无希望——主要问题只是如何付诸实践。”(第144页)对于马呢尕查语使用者来说,首要任务依然是个体与群体在西藏内外共同努力,持续推动语言重拾。
英文原文:https://melbourneasiareview.edu.au/the-politics-of-language-oppression-in-tibet-by-gerald-roche
原文发表于《墨尔本亚洲评论》第二十一期,2025年3月3日
原文DOI:10.37839/MAR2652-550X21.13
图片:西藏卡若拉冰川(Karola Glacier)下,摄于2024年。来源:杰克·麦克马洪(Jack McMahon)。书封经出版商许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