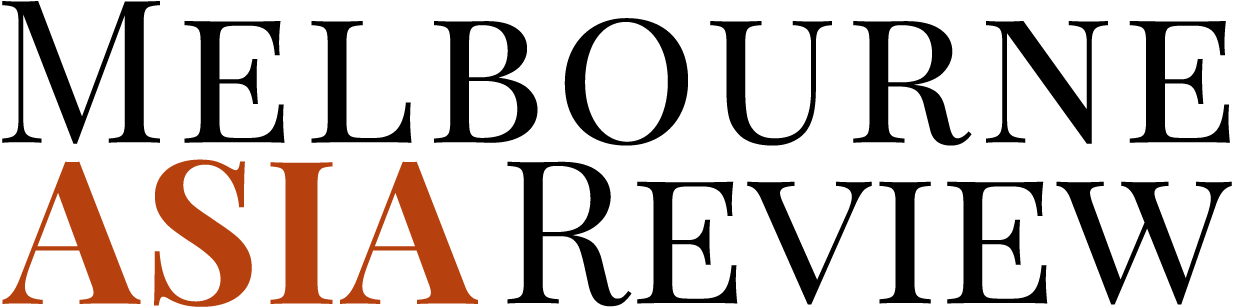译者:韩昕洋 (Xinyang Han)、陈春晓 (Chunxiao Chen)、叶思怡 (Siyi Ye)、衣泠梦 (Lingmeng Yi)
翻译审校:魏安天博士(Dr Anthony Williams)
斯里兰卡是一个位于印度南边的岛国。自1948年独立于英国以来,斯里兰卡语言多样性的管理在政策和实施层面上都备受考验。
斯里兰卡的主要人口是僧伽罗人,讲僧伽罗语。泰米尔人则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少数民族,讲泰米尔语。斯里兰卡宪法将这两种语言都定为斯里兰卡的国家官方语言,英语则被冠上“交流语言”的模糊头衔,其他语言均未具体提及,它们的存在均未得到任何形式的承认。
困难重重的近代史
自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后,认定国家官方语言的道路十分曲折。泰米尔分裂分子和斯里兰卡国家安全部队之间的暴力冲突持续已久,实际上其核心争端就是语言权利。斯里兰卡自由党通过《官方语言法案》(1956年第33号)宣布僧伽罗语为唯一官方语言这一举措,导致了该争端的出现。虽然泰米尔语随后也被认定为官方语言之一,语言平等仍然是斯里兰卡面临的一大问题。在冲突后的背景下,有人建议斯里兰卡采用三语政策:第一语言(僧伽罗语或泰米尔语),第二语言英语,僧伽罗语或泰米尔语互相作为对方语言群体的第三语言。然而,这一政策的实行并不成功。
尽管在斯里兰卡还有一些使用人数较少、知名度低的语言,在上述两种主要本地语言及英语三者之间争夺承认与权利的背景下,几乎没有空间讨论这些较少使用的语言的保护问题。然而,由于斯里兰卡仍在力求在各个不同族群间建立实质性且持久的和谐关系,学习这些较少使用的语言并致力于其保护,便至关重要。因此,通过分析国家官方文件,如斯里兰卡宪法和人口普查文件,以及国家机构在语言政策制定中的角色,本文对斯里兰卡当代语言现状与该国保护使用较少的语言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探讨。
使用较少的语言
尽管学者们认为斯里兰卡至少有11种语言,并且世界语言数据库“民族语”显示斯里兰卡现存的语言有5种。然而,如前所述,宪法只提及了僧伽罗语、泰米尔语和英语这三种语言。宪法不承认使用较少的语言这一做法,对较大族群对这些语言的认知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族群普遍将规模较小的语言视为“次要语言”。对于维达(Vedda,亦称“阿迪瓦西”(Aadivasi))、泰卢固(Telugu)、罗迪(Rodi)等因各种社会历史和社会经济因素而被边缘化的族群,这种负面影响尤为严重,同时还进一步影响了族群成员自身对其语言的看法。例如,在斯里兰卡马来族群的案例中,作者的实地考察显示,有许多马来家长认为:相比于设法习得英语及僧伽罗语,或是其中之一,保护马来语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英语和僧伽罗语才是决定孩子未来的关键。这种观念恰恰危害了使用较少语言的未来,因为语言使用者对于其母语的态度,正是决定该语言能否在未来世代中传承下去的关键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口普查作为另一个主要的国家工具,进一步使局势恶化。斯里兰卡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局采用的方法存在以下严重问题:
首先,统计中没有单独列举各族群所使用的语言。在缺乏各语言使用人数的独立数据的情况下,学者和语言社群成员往往依赖与族群相关的数据,尽管这就假定族群总人数与该族群语言使用人数之间有直接关联。但此做法其实存在问题,因为这种简单的混为一谈并不适用于实际情况。例如,在跨族群婚姻中,人口普查会根据父亲的族裔来记录母亲和孩子的族群归属。然而,这样的家庭所使用的不一定是父亲的语言。因此,只有对家庭语言实际使用的详细调查才能反映出其真正使用的一种或多种语言。
其次,斯里兰卡人口普查仅涵盖了七个族群的数据,但实际上,国家内部还存在许多少数族群,而关于这些族群的人口信息却被简单地归入到“其他”类别。不论在实际划分和意识形态层面,统计局的这一做法都存在问题。从实际划分角度来看,笼统的归类方法使个别族群的相关数据变得难以获取,从而造成其面临的特定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即使能为这些族群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也缺乏必要的数据。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未被单独列出意味着众多族群的独特身份和历史没有被国家承认。例如,斯里兰卡的原住民社群——“维达人”(Vedda,亦称“阿迪瓦西人”(Aadivaasi),内部成员自称为“森林之人”(Vanniyala Eththo)),虽然被视为斯里兰卡土地的最早居民,人口普查原本将该族群单独列为一类,但在1963年之后,他们却被归入“其他”类别。这种归类使自我认同为维达人或阿迪瓦西人的具体人数变得难以统计,从而也无法统计使用该族群独特语言(目前被认为是濒危语言)的人数。这对斯里兰卡最古老的社群而言,是一种严重的不公。不承认“较小”族群的另一个后果是,这些族群的独特历史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抹去,或被更大的族群所同化,例如,阿迪瓦西族和罗迪族正在逐步被更大的僧伽罗族和泰米尔族同化。
在斯里兰卡的宪法和人口普查中,过于笼统的归类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意味着:只有宪法中提及的三种主要语言,以及人口普查中单列的七个族群才被赋予重要地位,而那些使用人数较少、知名度较低的语言及其使用者却被自己的国家视为边缘公民。
在斯里兰卡某些领域中,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这些少数族群的边缘化现状及其语言的濒危问题,原因如下:一、 宪法未承认或承诺保护使用较少的语言;二、 各种语言的使用者数量未被单独统计;三、人口较少的族群被统一归入“其他”类别。
使用较少语言所面临的社会与语言威胁
阿迪瓦西语作为斯里兰卡最古老的语言,目前正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主要原因是这种语言很大程度上正被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同化。并且,与其他一些较小的族群不同,阿迪瓦西族属于弱势族群,其传统生活方式与其语言都面临消亡的威胁。随着越来越多的阿迪瓦西人为了就业和更好的经济前景而迁离原居住地,阿迪瓦西聚居地的数量正在减少。这种人口流失对语言的保护造成了直接影响,因为迁移者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为了提高就业机会并融入更大的社会群体,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族群的语言,转而使用僧伽罗语或泰米尔语。
另一个正面临未来不确定性问题的流动族群是泰卢固族(亦称“库拉维尔族”(Kuraver),曾被称为斯里兰卡的“吉普赛人”)。该族群使用的语言是源自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泰卢固语的变体,目前尚未得到充分记录,也未受到任何有效措施的保护。
罗迪族及其语言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罗迪族是僧伽罗族群中一个被认为是“低种姓”的亚群体,该群体因种姓歧视而备受苦难。尽管在1957年,斯里兰卡政府已经立法禁止了种姓歧视,并在1971年的修正案中规定了对歧视行为的严厉惩罚,但针对罗迪族的歧视问题仍未完全得到解决。
在某些情况下,族群成员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想方设法保护本族群语言。有时语言保护工作也能得到对各族相关语言和文化感兴趣的国内外学者的支持。外国访问学者与当地族群之间建立的关系,通常会带来语言保护的积极成果。斯里兰卡马来语和斯里兰卡葡萄牙语便是典型的例子。比如,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通过将古老的马来语文献数字化推动了对斯里兰卡马来语书面语言的保护,从而为斯里兰卡马来族做出了独特且宝贵的贡献。这一举措促使许多定居海外的斯里兰卡年轻人开始关注自己族群和其语言的历史。这些年轻侨民目前正在讨论如何通过语言保护来帮助斯里兰卡马来族群增强其身份认同感。
以斯里兰卡马来语为例,斯里兰卡马来社群与马来西亚高等委员会、驻科伦坡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合作,为社群成员提供马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课程服务。然而,语言标准化这一关键问题在此类合作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马来语是一种多中心语言,具有多种不同的方言变体,分别在不同的马来语国家中使用。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语被称为Bahas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语),在马来西亚,则被称为Bahasa Melayu(马来语)。
在斯里兰卡使用的马来语被称为斯里兰卡马来语(Sri Lanka Malay, SLM),是一种独特的变体,吸收了大量马来词汇,句法系统相当复杂,具有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的语法特点,既不属于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语,也不属于马来西亚的马来语。在保护该语言变体方面,族群成员面临诸多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教授印度尼西亚马来语和马来西亚马来语的价值仍有待商榷。然而,相关外国驻斯使团的介入引起了一个关键问题:应该保护的究竟是马来语哪一变体?是“最原始”的、所谓“标准”的印度尼西亚语或马来西亚语,还是本土的斯里兰卡马来语?对于斯里兰卡马来语的未来来说,这样的争论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以斯里兰卡葡萄牙语族群为例,雨果·卡多佐教授(Professor Hugo Cardoso)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尤为值得关注。他们对该族群的语言和诸如歌舞等文化实践的记录工作,使得本族群成员对此方面的兴趣日益增长。如今,斯里兰卡葡萄牙语族群的音乐和舞蹈在首都科伦坡(Colombo),甚至在海外均有所展示。
还有一些规模较小、从事贸易的族群,他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印度——这些族群在19世纪末印巴分治期间迁移到了斯里兰卡,他们的语言如今正处于濒危境地。这些族群成员为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对自身语言的未来表示担忧。其中一个族群是斯里兰卡的梅莫斯人(Memons),他们的语言梅莫尼语(Memoni),融合了信德语(Sindhi)、乌尔都语(Urdu)和古吉拉特语(Gujarati)的元素。全球约有150万梅蒙人使用这一语言,尽管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但斯里兰卡梅蒙人(人数约为5000)担心,他们的本族语言在斯里兰卡正面临濒危的威胁。因此,为了振兴本族语言,该族群的成员正通过多种方式评估族群的语言流失程度,如开展问卷调查、访谈,以及进行语言活力测试,同时,他们也计划引入技术媒介工具来遏制已被察觉的语言衰退现象。
斯里兰卡的达乌迪博拉(Dawoodi Bohra)族群也有着相似的历史。该族群使用的语言为道瓦特语(Lisan-al-Dawat,更常见的名称为Dawat-ni-zaban)。这种语言融合了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和古吉拉特语的元素,并使用阿拉伯文字书写。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设有一所博拉(Bohra)族群学校,尽管该学校的主要学术课程以英语为教学语言,但校内仍设有教授道瓦特语的课程。因此,与语言使用人数较少的族群相比,达乌迪博拉族对语言消失的担忧程度较低。
斯里兰卡也是一个祖先源自非洲的小型族群的家园。他们是非洲布尔格人(African /Afro Burghers),过去曾被称为“卡菲尔人”(Kafirs)。但如今该族群拒绝使用“卡菲尔人”这一称呼,因为他们认为此称呼带有历史性的贬义。非洲布尔格人以其独特的舞蹈和音乐而闻名,且由于族群中大多数人的祖先是曾被葡萄牙殖民者作为奴隶带到斯里兰卡的非洲人,他们使用的斯里兰卡葡萄牙语还夹杂着一些源自非洲的词汇。由于失业问题及随之产生的经济困难,这一族群的未来处境堪忧。
国家层面的回应
与印度不同,斯里兰卡并没有专门致力于推广、教授和研究小语种的国家机构。目前,斯里兰卡在语言方面的三个国家机构分别是:斯里兰卡官方语言委员会(Official Languages Commission)、斯里兰卡官方语言部(Department of Official Languages)和国家语言教育与培训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其中,斯里兰卡官方语言委员会的职能是:“规范和监督《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四章所列语言权利的相关条款的落实情况”。
斯里兰卡官方语言部负责提供翻译服务,以及编写词汇表、教科书和词典,并开展语言推广项目,以支持国家官方语言政策的实施。值得一提的是,该机构的一个目标是:“培养精通僧伽罗语、泰米尔语、英语和外语的人才,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因此还开设了法语、德语和日语课程。然而,当高级政府官员被问及为何无法将斯里兰卡小语种的保护与推广纳入其职责范围时,他们通常表示没有相关权限,因为其职责仅限于保障和推广宪法中明确列出的语言。但官方语言部既然推广外语,可见政府还是愿意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在官方语言政策之外进行扩展。由此看来,小语种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推广它们并不会给国家带来经济效益。
第三个负责语言发展的国家机构是国家语言教育与培训学院。该学院成立于2007年,旨在为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教师提供支持,并为宪法中所列明的三种语言——僧伽罗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培养合格的翻译员和口译员。显然,小语种之所以被忽视,再次可归因于它们并未被纳入宪法。
语言描述与记录(Language Description and Documentation,简称LDD)是语言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前文所述,在斯里兰卡,目前没有授权任何国家机构对小语种开展大规模的语言描述与记录工作,政府也没有就语言与文化保护问题与小族群展开对话,这些语言和族群的系统性、科学性研究也远未被列入非政府组织的议程。因此,除了少数有兴趣的学者开展的零星研究外,这些语言始终处于研究空白状态。这种情况不仅严重危及这些语言的未来发展,也对这些语言使用者的集体认同感造成深远负面影响。
结论
目前,斯里兰卡正站在现代历史的新起点上,国家由人民党(NPP)充满活力的阿努拉·库马拉·迪萨纳亚克(Anura Kumara Dissanayake)及其政府执政,迪萨纳亚克是国家自独立以来第一位偏左社会主义总统,他的政府承诺要“为所有族群创造一个共同想象未来的空间,建设一个团结的斯里兰卡国家”,为国家带来了迈向新时代的希望。然而,新政府面临的挑战极为严峻:国家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创下新高,人民对一届又一届既腐败又效率低下的政府早已心灰意冷。此外,族群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虽表面平静,却始终暗流涌动,且时常被宗教人士或投机政客煽动,以谋取私利。新政府当选的主因之一,是他们承诺将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其中族群多样性将被尊重与颂扬。现在,他们必须证明自己不仅有能力兑现承诺,更有意愿真正实现这一承诺。
图片内容:斯里兰卡科伦坡。图片来源:Flickr/tbz.foto.
原文发表于《墨尔本亚洲评论》第二十一期,2025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