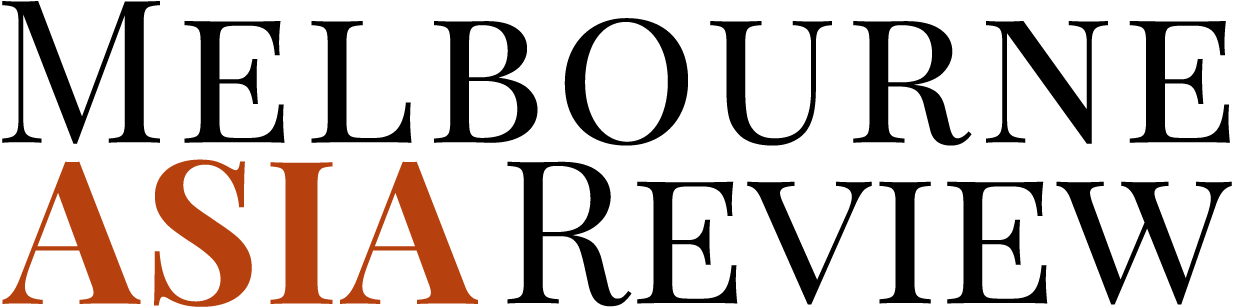译者:李鑫(Xin Li) 金益羽(Yiyu Jin)
1995年,台湾酷儿文学作家纪大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感官世界》,由平氏出版社在台湾以繁体中文发行。紧接着,他的第二部作品《膜》于1996年由联经出版社出版。两年后,他的第三部作品《恋物癖》经时报出版社推出。这是台湾酷儿文学“百花齐放”的时期,纪大伟与陈雪、洪凌等作家作为先驱者,通过文学作品“打破了人们对性别和性向认同的刻板印象,为台湾酷儿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不是单纯地宣扬同志的正面形象。”
纪大伟与他同时代的酷儿文学作家掀起了一场全新的文学运动,这一运动后来被纪大伟本人定义为“台湾同志文学”。这种文学类型由“以同性恋为题材的作品”构成,并且“经常被赞誉为对非西方社会中更具压迫性的环境进行抗争的范例”。这一文学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出版的英文译本,以及如马嘉兰(Fran Martin)和刘奕德 (Petrus Liu)等学者的先锋性英文研究著作,这些著作主要聚焦于1990年代台湾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的酷儿文学。
尽管纪大伟在台湾同志文学史上的影响力毋庸置疑,而且他的文学作品在台湾和大陆一直处于华语酷儿文学的核心地位,但台湾酷儿文学的出版、传播和接受情况在大陆却鲜少受到关注。直到 2003 年初,《膜》(包括同名短篇小说《膜》和《嚎叫》、《早餐》等九篇短篇故事)才由华艺出版社在大陆出版,这是纪大伟的作品首次以简体中文形式面世。2012 年,大陆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重庆出版社出版了《膜》简体字删减版。
作为一名来自大陆、现居澳大利亚的酷儿学者和译者,我自2000年代初开始阅读纪大伟的作品,并对中文同志/酷儿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重新阅读纪大伟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早期小说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本文中我将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着重探讨纪大伟的短篇小说《早餐》和《嚎叫》。2020年,我将《嚎叫》从中文翻译成英文时,结合了对酷儿文学和翻译研究的兴趣,探讨了台湾与大陆同志文学之间的联系,同时认识到了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并避免将两者混淆。
纪大伟在台湾和大陆的文学历程简述
在1990年代的台湾,全球化与本土化紧密交织,尤其是在性别和性方面。在这一时期,随着酷儿运动的兴起,台湾历史上关于性别与性观念经历了最深刻的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纪大伟首次采用诱惑性、挑衅性和狂欢式的语言与叙事风格,以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异性恋主流观念以及对艾滋病(毒)的社会污名化。在这一年代,纪大伟在台湾出版了《感官世界》(1995)、《膜》(1996)和《恋物癖》(1998)三部文学选集。这些文集中的许多短篇小说通过描写恋物癖来“颠覆、挑战和抵抗传统的性别角色以及异性恋主流观念。”同时也突显了将深植于地方历史和文化中的亲密关系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困难。他的短篇小说《嚎叫》(1998年,2021年Yahia Ma译为Howl)和《香皂》(1995年,1998年马嘉兰译为The Scent of HIV)就体现了这些翻译挑战。
在同一时期,与酷儿相关的新术语、新短语和新知识逐渐出现,例如“同志”(tongzhi)和“酷儿”(kuer),这些词汇后来成为台湾、香港、大陆以及中英文翻译中被广泛接受的表达形式。1994年,在纪大伟、洪凌和但唐谟共同编辑的《岛屿边缘》期刊的酷儿专题中,“queer”一词被翻译为“酷儿”(ku’er)。纪大伟对“queer”一词的翻译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一期刊封面上的中英文双语标题“酷儿QUEER”可能是“酷儿”首次作为“queer”的翻译在台湾出现。这一专刊的出版时间恰逢尚·惹内 (Jean Genet)的《窃贼日記》和马努叶·普易(Manuel Puig)的《蜘蛛女之吻》两本中文译本出版,分别由洪凌和纪大伟翻译。该专刊长达近 70 页,内容包括了两部外文小说的译者序言和原著节选,以及一篇题为《小小酷儿百科》的文章,文中有49个条目,插图疑似出自西方情色资源。
纪大伟在2000年代将他的短篇小说以简体中文形式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并出版短篇小说集,这显著提升了大陆地区对酷儿、艾滋病(毒)及相关文学的关注度和了解。纪大伟的短篇小说《早餐》和《嚎叫》也曾在大陆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包括由福建省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的《台港文学选刊》。福建省文学艺术联合会成立于1984年,旨在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整个汉语文化圈的文学作品介绍给大陆的读者。
2000年代初 我在大陆阅读《早餐》
纪大伟的开创性极短篇小说《早餐》在大陆多次印刷和收录在文集中,成为台湾
同志/酷儿文学中的一部代表作,并在兴趣网络社交平台如豆瓣上引发了热议。该作品创作于1999年,并在同年荣获第二十一届联合报文学奖极短篇小说奖首奖。2011年,此小说被收录于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的文学选集《膜》中。2018年,G点电视(G Dot TV)根据该小说制作了一部九分钟的粤语微电影。
这篇“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已婚男子与他情人的故事。每天晚上,丈夫总是和情人在外共度良宵;但第二天早上都会准时为妻子和儿子准备早餐。这个故事具有浓厚的酷儿色彩,因为它既没有明确情人的姓名或性别,同时又突出了其酷儿的特性。《早餐》故意避免使用传统姓名、性别和性取向的代词与描述方式,以保留故事中展现的欲望和身体特征的酷儿性,性别流动性以及性身份的多元性。
与纪大伟的其他作品不同,《早餐》几乎在出版后不久便在大陆发行。作为 2000 年代初的读者,我在《台港文学选刊》中读到了这篇小说。它为我提供了一种逃离当下现实的途径,开启了我对自身性取向和欲望的探索。《早餐》促使我理解性别和欲望的模糊性与流动性是如何相互交织的,并展示了如何创作出如此强有力且非常规性的酷儿小说。
如今回想纪大伟的作品,各种与性别议题、身份认同和相关知识浮现在我脑海中。这些内容来自21世纪的当代中国,正如文化与媒体研究学者包宏伟在《酷儿中国:后社会主义语境下的酷儿文学与视觉艺术》中指出的,随着越来越多的酷儿场所、组织、资金来源,以及公开或非公开的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出现,中国城市的酷儿文化和社会氛围正发生变化。当时,作为一名生活在内地小镇的高中生,我正在艰难探索自己的性别认同和性取向,却对外界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也不理解什么是性、性别、性取向或各种关系。
作为一名读者,我通过阅读大陆的一本主要文学杂志上纪大伟的短篇小说,进行了一种无意识的抗争。我向父亲请求,通过当地的中国邮政订阅这本杂志,尽管当时经典的西方文学翻译作品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受到强烈推荐,我却依然选择去阅读纪大伟的《早餐》。
在研究台湾酷儿文学的过程中,我从《早餐》中获得了重要的见解。正如文化研究学者马嘉兰在2011年英文版《膜》后记中所提到的,纪大伟的性主题“存在于军事、教育、医疗和家庭系统等诸多空间中”,同时也体现于当代台湾的城市
社会文化领域,比如便利店、咖啡馆等频繁出现的场景。她还指出,纪大伟的故事“展示了如何‘酷儿化’这些日常时刻,揭示了不可预见的欲望如何为平淡无奇的生活注入令人惊奇的新活力”。
在疫情期间翻译《嚎叫》
《嚎叫》最早以繁体中文发表,收录在1998年台湾出版的小说集《恋物癖》中。2003年,这篇小说以简体中文收入《台港文学选刊》,并在大陆出版,同时也被收录在同年华艺出版的《膜》中。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讲述了居住在“只有一扇小窗户的小公寓”中的叙述者,与一个绰号叫 “阿米巴”(全名是□ □ □)已感染了艾滋病毒的男子发生了短暂的 “无性 ”邂逅。他们最初在一个名为“San Francisco”的密闭咖啡馆相遇,随后进入一条卤素灯泡汇集的隧道,紧接着又前往小巷里一间隐蔽的便利店,最后回到家中,阿米巴从狭小公寓内的浴室进进出出。
《嚎叫》和纪大伟的其他许多短篇小说一样,核心要素之一是对艾滋病时代爱情语言的阐释,这种阐释通过恋物癖的方式对抗恐同和艾滋病污名化的社会氛围,从而打破了性别、性和性取向的传统界限。按照我现在的理解,《嚎叫》通过“恋物化”和“反常”的视角,展现了男性身体的多维度酷儿特征,比如受艾滋病影响的身体或身体的气味。早在 2000 年代初,我第一次在《台港文学选刊》上阅读这篇故事时,它让我对欲望、性和艾滋病的另类知识有了细致入微的了解。这些知识是我高中生物老师在性教育课上没有讲到过的,我们只能从课本上自学,学得满脸通红,心跳加速。2020年初,在新冠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之前,我受托将《嚎叫》从繁体中文翻译成英文。
在中国疫情封锁期间,由于澳大利亚自2020年3月20日起禁止所有非公民和非居民入境,导致我无法预见何时能以学生签证返回澳大利亚,我当时已在澳大利亚开始修读硕士课程。在翻译《嚎叫》的过程中,我在两种中文版本之间来回切换:一版是2003年在大陆出版的简体中文版,另一版是我的委托编辑发来的繁体中文版电子文档。在翻译时,我仿佛在台北和旧金山之间穿梭。故事全文贯穿了各种符号和标志,包括墙上喷涂的和平标志、艾伦·金斯堡的《嚎叫》黑白封面上的“O”变成了☮、印满玫瑰的牛奶糖包装、软木垫上的备忘录(便利贴、披萨店折价券等)、扎染彩虹T恤、闪烁着 “San Francisco”字样的霓虹灯,以及金斯堡《嚎叫》的英文引文。
正如标题所暗示的那样,纪大伟在作品中反复提及金斯堡。虽然在一开始,对金斯堡的描绘似乎只是偶然为之,但仔细阅读便能发现,这正是酷儿研究学者李· 埃德尔曼(Lee Edelman)所说的“关键的抹名”,而这种抹除“从未摆脱认识论(我们如何去理解和定义事物的方式)与‘柜中身份’(隐瞒自己真实身份的状态)之间的相互影响”。然而,这种对名字的抹除在保护阿米巴性身份和艾滋病毒感染者身份的同时,也揭示了“柜子”的悖论:它激发了人们对出柜的恐惧(谁又愿意和阿米巴上床呢? 尽管 “不会从他身上沾来什么病毒”);它使无名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以一个脆弱的形象进入文本(“太强的力道是不是会捏碎这具瘦小的人体”);它与第一人称叙述者(与纪大伟本人一样,他也是一名作家,并以在台北的San Francisco咖啡馆游荡为乐,同时在那里写作)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这位匿名的 “阿米巴”是一位画家,一位金斯堡的读者,一位在台北的San Francisco咖啡馆游荡的涂鸦艺术家,一位梦想家;他渴望 “在旧金山湾画满玫瑰”,渴望在旧金山 “脱光衣服享受日光浴”。
在故事的高潮部分,第一人称叙事者将无名男子□ □ □带回家,并看到了他的身体。作为酷儿译者的我,也进入了文本,享受翻译这一非常规身体的过程,体会其脆弱、瘦弱以及艾滋病毒感染的状态。我(第一人称叙述者和译者)“用拇指和拳头挤捏他身上多处部位”,这让他 “频喊痛快”。我(和“我”)只见“寻常的器官,颜色形状尺寸都不算特异”,触摸身体让“我”思考,“这可就是桥梁吗,一头是快感的天堂,另一头是煎熬的地狱?”金斯堡可能会将这种相遇称为“carezza”,用他的话说,这是 “一种柏拉图式的友谊,人们赤裸相拥而眠,彼此抚摸,但不达到性高潮,因精神修行或其他原因避免射精”。
2021年年中,我的《嚎叫》英文译本正式出版。我收到了一本经过中国邮政辗转多地,最终送达大陆的实体书。在东安格利亚大学暑期翻译课程期间,我与来自美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新锐翻译家们以远程方式参与了“台湾文学工作坊”。当时我正在翻译《早餐》,与著名的酷儿译者程异在线合作,他从美国指导,而纪大伟则从台北在线参与。
纪大伟作品的长期影响和价值
2021 年 12 月中旬,我回到澳大利亚。纪大伟199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膜》已经由韩瑞翻译成英文,译者认为,尽管这本书早在1995年就首次出版了,但它却“以惊人的准确性预测了当代关注的问题”。为了庆祝此书译本的出版,纪大伟于2023年12月10日来到达令赫斯特书店,与来自澳大利亚、大陆、台湾及其他地方的读者汇聚一堂。通过热烈的讨论,我们各自分享了对纪大伟1990年代作品的不同观点,进一步加深了读者之间的理解与联系。
重读纪大伟20世纪90年代的酷儿故事,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和感受酷儿文学如何将语言、文化和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从而塑造我们对汉语中“酷儿”这一概念的理解。回顾那些引领我们走到今天的时刻,真是奇妙。在这大陆、中国台湾、澳大利亚及其他地方的酷儿译者、学者和读者相聚的时刻,回溯到二十年前我在孜孜不倦地阅读《早餐》和《嚎叫》,那时的我对未来一无所知。
图片来源:解读1990年代的酷儿文学 Yahia 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