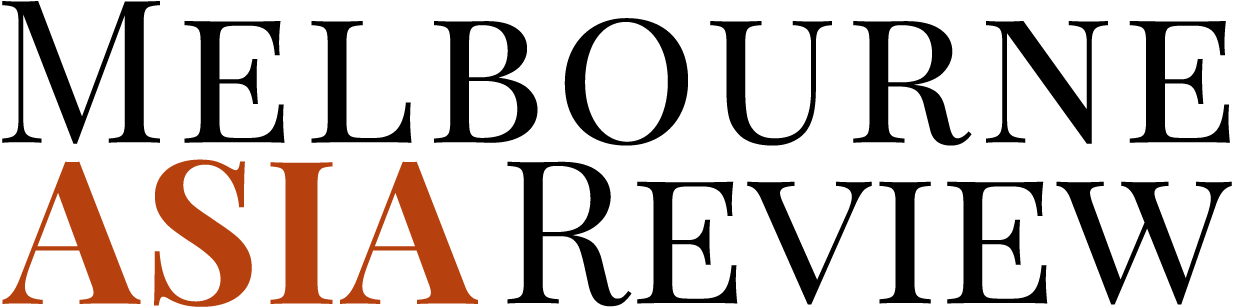译者:李欣羲(Alison Li)、蔡泽森(Zesen Cai)、刘柯岑(Kelsey Liu)
翻译审校:魏安天博士(Dr Anthony Williams)
澳大利亚员佐勋章获得者卡罗琳·休斯博士(Dr Aunty Caroline Hughes)是恩古纳瓦尔(Ngunnawal)语族长老,在原住民社群中备受尊敬。她认为:“语言是生命万物的内在部分。它对于我们传递价值观、信仰以及习俗至关重要。它启示并指引我们履行社会角色,而且培养我们的群体认同感,让我们团结一致。然而,当我们不被允许使用自己的语言时,这一切便出现了裂痕。”
语言的多样性、边缘化与流失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统计,全球约有7000种语言,有一半处于濒危状态,而其中有3000种语言正面临灭绝的风险。这些数据凸显了语言流失问题的严重性,也显示出采取积极行动的迫切性。
亚洲也不例外。据估计,亚洲目前使用的语言约有2300种。然而,许多语言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这是因为各国的语言政策倾向于重视主流语言,而忽略地区语言和少数群体语言。在笔者所在的国家——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的现况也令人十分忧心。根据《2020年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报告》(National Indigenous Languages Report, 2020),在殖民时期前,澳大利亚原住民所使用的语言超过 250 种。然而,2016 年人口普查显示,如今仅剩约159 种原住民语言仍在使用中,而令人更加担忧的是,全部无一不面临流失的风险。
殖民主义留下的历史遗产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例如,英国在亚洲的殖民统治确立了英语在印度、新加坡及香港等前殖民地的行政、教育与商业语言地位,奠定了英语日后持续的全球主导地位基础。殖民主义将英语作为治理工具与文化同化的手段,导致当地语言被边缘化。此外,许多亚洲国家为了推动国家发展以及加强民族认同感,实施了有利于其主流语言的政策,以凝聚多元社群并提升国民识字率。然而,此举措却进一步压缩了少数群体社群语言的生存空间,导致这些语言被边缘化。
语言濒危与流失的后果
尽管语言的变迁与转用属于文化演化的自然过程,但是如今语言多样性的快速削弱,却在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推动下大幅加剧。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文化认同感与社会凝聚力的核心支柱。另外,多语能力亦有助于提升认知能力,加强人们应对复杂社会情境的能力。
语言的多样性不仅赋予人们对自身身份与文化的自豪感,更能促进团结,而并非造成分裂。当原住民或少数群体的语言消失时,使用该语言的社群也随之失去了数百年来累积的丰富知识,以及了解其历史、文化遗产与价值观的宝贵途径。
语言流失也会对教育产生深远影响。它中断了知识的代际传承,削弱了社群之间的联系,并导致了更广泛的文化贫乏,从而削弱了全球共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一份政策报告显示,非母语的授课形式将影响儿童基础读写与基础算数的能力发展。全球有多达40%的人口无法以完全理解的语言接受教育,这一障碍进一步扩大了学习差距,加剧贫困,并持续了边缘化的恶性循环。
在本期专刊中,各位作者强调了亚洲各地社群所面临的挑战。他们聚焦于亚洲各国中经常被忽视的语言多样性,并分析了加剧语言边缘化以及推动语言复兴的各种因素。
Dr Trang Thi Thuy Nguyen探讨了语言殖民主义在越南留下的影响。当地的教育体系将越南语置于优先地位,导致如嘉莱族人(Jarai)在内的少数族裔学生遭受系统性的边缘化。罗莫拉·拉苏尔博士(Dr Romola Rassool)分析了斯里兰卡的语言政策,尤其关注各语言在宪法中未被纳入、在人口普查中未被统计的现状,并且探讨了这些因素如何导致少数群体语言被边缘化,进而破坏族群之间的和谐,并削弱各族群的文化维护能力。
何彦诚教授(Professor Yancheng He)与罗永现教授(Professor Luo Yongxian)以类似的视角研究了中国濒危的仡佬语的衰退状况。该研究指出,仡佬语的衰退源于文化与语言同化、经济压力以及倾向于推广国家语言(普通话)的教育政策,同时也强调了一些有望推动语言复兴的语言维护措施,包括广泛的田野调查、社区语言项目和详尽词典的编纂等多项努力,这些措施旨在给这项独特的语言遗产重新注入活力。此外,兹芭·阿克巴里(Ziba Akbari)聚焦中东地区库尔德族人(Kurdish people)的处境。由于库尔德族人并未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正面临跨国界的系统性压迫。阿克巴里进一步说明,这种边缘化如何导致了库尔德族方言的分裂,并严重削弱了该民族的文化存续与身份认同感。
语言复兴:为公义而奋斗的努力和挑战
在面对语言多样性的严重衰退的同时,全球正逐步兴起一股促进濒危语言复兴的运动。联合国推动的“国际原住民族语言十年”(2022-2032)(International Decade of Indigenous Languages,2022-2032)等倡议,旨在将语言视作重要文化遗产并予以认可与维护。这些努力不仅呼吁维护语言多样性,更致力于解决与语言流失和濒危并行而来的社会与教育不平等问题。
语言复兴的努力是多方面的。法兰吉丝·加德里博士(Dr Farangis Ghaderi)与约安娜·博黑恩斯卡(Dr Joanna Bocheńska)所探讨的中东地区库尔德语文学与文化行动主义便是其中一个实例。加德里博士的文章记录了从广播、音乐、戏剧、电影到学术领域等多方面的语言复兴努力,强调数位行动主义在为库尔德语使用者创造一个可见且充满活力的文化空间中,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艾瑞·库尔尼亚万教授(Professor Eri Kurniawan)和迈克尔·犹因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Michael Ewing)对印度尼西亚巴杜伊族人(Baduy)社群中的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并强调了现代化的影响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例如旅游业的发展、与印度尼西亚主流社会接触的增多,以及外部的政府压力。两位教授还展示了一些专项语言复兴项目下对独特巴杜伊语所作的成功语言维护工作,其中包括合作型语言记录和创新的媒体项目。
在中国,国家统一与语言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尤其显著。蒂姆·瑟斯顿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Tim Thurston)指出,尽管国家支持的文化遗产项目,比如《格萨尔史诗》(Gesar epic)的推广,为藏族文化传统提供了一个展示平台,但这些项目对藏语的日常使用和维持几乎起不到任何支持的作用。亚历山大·格雷博士(Dr Alexandra Grey)也同样论述了中国不断演变的语言政策如何体现出其相互矛盾的政策倾向:虽然政府在不断加大推广普通话的力度以促进国家统一和经济一体化,但诸如“语保”项目等政府举措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记录少数民族语言,而不是促进其日常使用。这两个例子都体现出语言多样性名义上的维护与语言同质化实际追求之间的矛盾。
在日本,语言复兴同样面临重重挑战。杰弗里·盖曼教授(Professor Jeffry Gayman)和萨那·桑塔拉赫蒂(Saana Santalahti)批判了日本政府对阿依努传承文化和语言的现行政策。他们认为,尽管日本政府有在努力推广阿依努文化的“理想化意识”,但这些努力并未能解决系统性的问题——从日本北部岛屿北海道的殖民历史,到实质性语言支持和语言权利的缺失。因此,他们呼吁日本实质性地承认阿依努文化并进行政策方面的结构性改革。
在海外社群中,语言维持也成为可保持文化韧性的一个重要策略。例如,在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松井·美也子博士(Dr Miyako Matsui)和折山·佳耶博士(Dr Kaya Oriyama)探讨了社群语言维持中一个较少被关注到的方面——父亲在日语代际传承中的角色。通过对跨国婚姻家庭的案例研究,作者呈现了关于家庭语言实践和语言意识形态的复杂情况。他们认为,父母的能动性在语言维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应当与社会和机构的支持相结合。
语言复兴,归根到底是一场争取社会公义的斗争。语言流失问题是与历史的不公和系统性的歧视密不可分的,而且这些不公和歧视仍在继续边缘化原住民。通过主要强调多语种教育及多语种使用、社群主导的语言复兴,以及公平的资源分配,我们可以逐步消除已危及无数种语言的压迫性制度问题,从而确保语言多样性持续成为全球社会公义广受赞誉的基石。
结论
本期专刊从多个角度探讨了亚洲语言多样性危机和为语言复兴所作出的努力。无论是通过原住民语言的濒危现状、越南教育体系下的边缘化问题、斯里兰卡少数族群语言的困境,还是中国和日本尤为复杂的政策环境,本期的文章共同突显了影响语言濒危现状和语言活力的多种推动因素及其具体表现。其中一些推动因素源于国家的管控机制、人口迁移的加速流动以及通讯技术的进步。这些文章还强调了语言不仅是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和历史的载体,同时更是争取社会公义的关键要素。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确保每个社群都能使用其本族语言,对于促进社会凝聚力、维护文化尊严和推动真正的包容来说至关重要。本期专刊呼吁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和各社群积极支持多语种教育,推动家传语言与本族语言的维护,并赋权于全球多元社会中那些不可或缺却被边缘化的声音,以此让亚洲那些被边缘化的语言最终得到更多关注。
图片:孩子们在蒙古的一所学校内玩耍。来源:World Bank/Flickr.
原文发表于《墨尔本亚洲评论》第二十一期,2025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