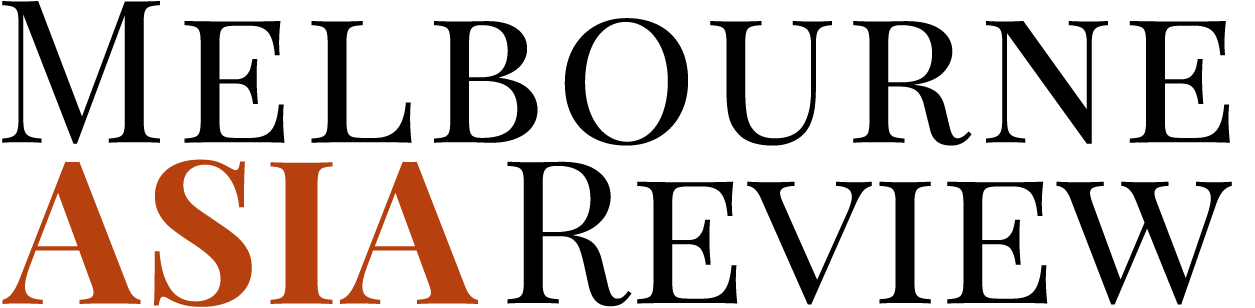林清美(Akawyan Pakawyan,1938年出生)是台湾原住民的卑南族人,也是南王部落族长。
林清美亲身经历了诸多重大社会变革,包括日本殖民时期(1895-1945年)到1945年中华民国(中国)控制台湾。这些社会变革都塑造和严重影响了原住民族群。在此之前,台湾原住民各个族经过1600年代荷兰人和汉族移民抵达西海岸的过程。
林清美一生则一直在努力地振兴原住民语言和文化,目前仍在台湾教育部担任卑南语课程的首席设计师,并在南王部落教授卑南语。此外,她还是台湾高山舞集的发起人和执行董事。
她接受了本刊执行主编凯西·哈珀的采访。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卑南族以及卑南族的文化。例如:主要的仪式和典礼,还有一些日常生活方式。
我们卑南族就十个部落。我们的语言是大同小异,十个部落都是差不多都可以沟通。我们卑南族一年有好几个祭奠仪式。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男孩子就是basibas,进阶的仪式结束以后就是我们的大年祭,这是我们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卑南族过年的一个仪式。然后大年祭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过年,那也就是说我们去打猎。这个是属于男孩子的一个技艺。Puwalresakan就是巫师他的旧的那个巫师袋,还要换新的,然后要开始启用那个新的巫师袋。巫师~我们的祭师在部落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那个地位,他们的工作也非常的繁重,当时保持部落的平安,对外要防止那个敌人,或者是要防止那个鬼攺,这些都是巫师的工作。
因为我常年当部落妇女会的会长,所以部落的所有祭典,不管是男女的一个,于是活动的时候,我一定会参加。那个自己的传统的那个祭仪,我认为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都会参加。

林清美的(Akawyan Pakawyan)(最右)跟其他舞蹈者包括Shura Taylor (右二) 2023年11月23号在墨尔本大学做出表演。经 Peter Casamento和墨尔本大学许可使用。
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卑南族人遭遇了什么?例如:可以反思一下对于语言和文化的影响,甚至是土地剥夺和宗教等问题。
日本人来了,他们想要改造我们做日本人,所以他鼓励那个家庭都要讲日语。那个时候一直都在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嘛,然后说我们没有学到多少。不过部落的人,老一辈的有很多都是那个讲日语的。这样的我们部落里面有好几家,但是我们从小就没有。。。我们还是讲我们自己的话。
日本时代,我在过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我唯一感觉到的。。。那就是我们没有东西吃,可能是战争的关系。那时候很难。衣服都没有。我小的时候,我都没有鞋子穿。文化方面的话,我们以前就是刺猴子,但是日本人他并没有禁止我们刺。在国民政府来了以后才禁止的。所以,在对我们的仪式,我没有感觉到说他(日本人)禁止我们什么。
对方说我们的山林,让他们(日本人)去想象我们的Patatallu这个土地,他们变成他们的军事用地,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是他们变成他们自己国家的土地。还有种甘蔗。种甘蔗是那个机场那一大片的一个地方。以前都是种甘蔗,种甘蔗的地方就变成真正那个日本政府国有地。因为不是在山上,我们都住在平地,所以呢,我们都没有跟他们有发生那个战争啊,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卑南族没有那个发生跟对方说像布农族啊,像邹族啊,他们都会一个抗战的一个。。。卑南族这里比较没有这样的冲突。
一方面是我们种植食物的改变。大量的那个水倒进来了以后,盖了水圳,灌溉,那大家都是种水稻,那就比较。。。没有人要去种小米的。因为没有种小米,就Misaur的妇女的工作团就消失了。
国民党取得控制权后,您们卑南族体验哪些变化?
我们部落,他(国民党)禁止我们就自己的话的一个权利。全国都实施国语政策。虽然他没有实施国语家庭,但是他这个禁止说方言的那个政策真的是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地方语言消失。老人家跟着小孩子去学国语啊,(老人家)他根本就没有教小孩子(地方语),他自己又在学国语不三不四的。发音不准的那个国语的时候,那真的是对我们语言的消失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我先补充一下我们土地流失的一个问题。闽南人好像经济头脑很好,是做生意的人。然后我们呢?比较憨,没有什么经济观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很容易受骗。我们的土地很大,那他们(闽南人)说:“这个土地太大,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租给我们?” 我们真的是很憨厚我们原住民,也可以说是没有经济观念,然后没有存钱的概念,没有储蓄的概念。土地那么大,我们够吃就好了嘛。。。我们不说要存着多少,没有这个概念。他们叫我们签字,我们肯定也看不懂还是怎么样。我们的土地就一直流失一直流失。到现在,没有土地的,没有几家。今天的台东棒球场以前是南王部落的一个坟墓,大家的亲人都是埋葬在那里,但是后来政府(国民党)说要收来做公用棒球场。现在,每一个家族的土地都分散到非常远的地方。然后,我爸爸生病很久,有一部分那边那个土地,也因为我爸爸的那个医药费我们也卖掉了那个土地,就一笔一笔的就卖掉了,我到现在我们一笔土地都没有了。
听到坟墓这件事情就感到很遗憾了。我想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比较正面一点……可以在重建语言和文化这两个方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认为个人最主要成就是哪些?
现在小孩子们在读书,要到外地去读书,就很少回来。那年轻人就变成对自己文化的自己的习俗,或者是自己的语言就不那么重视了。那回来我们的基本一直保存着,一直那个流传到现在,但是渐渐地就变成只有形式,没有内涵。小孩子呢,这样子跑跑跑。但是,真正的意涵是什么,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也因为这样子,而我们的语言有流失,我们的祭典仪式都流于形式方面的。因为我是读老师(师范学校)的嘛,所以我知道说一个自己文化的一个传承要靠教孩子。那我们做老师的话好像会有感觉,这个我要传承这个工作,我要祭典,仪式也好,要传承下去是我自己责任。
我现在本身的感觉就是我们的语言消失,那我们的文化也会消失,那我们的民族也会消失。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一直在心里深处有一种感觉说:“哪一天我们民族没有了”。我想天呐。。。我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在你们的手里我们自己的文化就消失了呢?这个其实我最深的感觉到的就是。。。有一种恐惧,一种很怕自己的民族消失。这个也就是我为什么成立高山舞集的目的,开始教那个族语。就是一种。。。可能我有这种使命感,我不知道傻傻的去做就这个。。。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教自己的歌谣,跳自己的舞,教(教导)训(训练)年轻人,从乐舞当中让他们认识自己的文化,也学习自己的语言。。。这种想法。那后来,好像以前刚刚开始的时那个闽南人呢,他们称我们番人。他们非常的歧视我们原住民。那感谢的就是后来那个像 “还我土地” 我们的年轻人大学生在台北啊,民歌民族运动。那他们就抗争“还我土地”,“还我传统领域”,像自己的民歌这些。我就是常常去游行,去抗争说“还我土地”呀,“还我语言”呀。后来慢慢的政府就成立了原民会,我们变成“原住民”。然后,才有那个教育法条的一个成立。然后,我们原住民族基本法那个能力慢慢慢慢慢的,现在就很重视要什么样子去复振我们的语言。那政府极力的,可能是花了很多钱在这个上面,在复振我们的语言,那本来我们就9族,后来就变成是12族,变成14族,现在变成16族。
大家就会回复自己原住民的那个身份的时候,那政府也慢慢的重视了我们台湾原住民才是我们的多元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比如,有个语言课叫“濒危语言的复振”。那个课就听老师一对一学自己的语言。这个是三年计划,这三年内你所教的这个年轻人一定要学会自己的语言。现在(有的在上过这门课程的学生)是政府议员的,那个原民台的那个政府议员。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我们争取了很多很多年。从一开始就。。。国民政府来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争取。民国九十年开始就他有认证考试,他就编教材。但是,也有些反弹。比如说原住民加分这个事情。其实加分这个并不是说抢走原先的名额给原住民,而是政府为了让原住民在没有其他汉人那么好的教育情况下来的,给他给它加一点名额而已。这是鼓励我们原住民的孩子,那个正在继续升学,还有升学的机会,让他知道那个读书很重要。但是,他到学校以后就受到歧视,他对他的心理的影响很大。别人说:“哦,你是加分进来的哦,但是你的课业,就是追不上别人的“。。。很多的人都会退学,就不读书了,或者出去工作,去学技术。
在我看来,您的一生经历了非同寻常的文化流动性……想问一下您自己是如何面对这种流动性的?为了要应对类似的挑战性差异的人,您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呢?
那个是我们不教的这些孩子们。那个时候他们还觉得这个自己的传统应该会练习。但是小孩子越来越没有兴趣,对自己的传统业务越来越没有兴趣。我就想:“哦对,在练习传统,他没有兴趣。那我。。。拿一个巴西的森巴鼓,让他们来练习,在练习休息的时间再带他们在练习自己的歌谣”。我用这个方法来纳入了这个森巴鼓的练习。你用这个森巴鼓前面做那个领导,然后我们就跟在后面。那个部落的人,那么就剩这个表演我们就来做一个表演。
结果就有人说:“领导是为什么,她(林老师)是那么传统的人,她为什么要引用新的东西?是国外的这个东西,这个声发出的敲击声管,为什么老师她会用到这个”。我就跟他讲:“时代在改变。那我们为什么不迎合年轻人的兴趣”?那我们有这种方法来带领小孩子们同时也有机会再去练习自己的那个古谣的时候。所以传统与现代会痛苦么?那就看看你怎么去那个吸引他们,这个是那个时候我的想法。传统是什么?我们就在这个议题上面,我们就要思考一下。我们永远是留在这里。。。自己永远都不在这个地方。
那国际交流。。。现在流通的是英语,那我们就找英语是怎么说?英语怎么说我们呢,我们就英语把他的发音稍微用我们的发音,来发音。我们尽量用我们自己的话保留我们的话,但是我们真的没有的新创词。我们用拼音,用英文字,写拼音罗马拼音,我们一直是罗马拼音。留下文字,我们的语言会留下来,我们的文化留下来、祭仪,很多很多动作,这些都会留下来。所以我现在就在拼命的做翻译的工作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就是要让现在的孩子要跟国际接轨,不要被孤立,不要被那个被变成孤独的,而变成排斥的。相信那个那么多发达我们没办法逃避,我们也逃避不了。我们也不能阻止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就随着时代的潮流,但是能够保留我们的自己的传统的文化,那我们就尽量保留。我们老人家还在,那我尽量告诉他们。
林清美的(Akawyan Pakawyan)助手及中英口译员Shura Taylor和Darcy Moore译者为本访谈提供了宝贵贡献。
林清美的(Akawyan Pakawyan)2023年11月23号在墨尔本大学Narm Oration年度活动发言。
主照片:林清美的(Akawyan Pakawyan)(中)2023年11月23号在墨尔本大学做出表演:经 Peter Casamento和墨尔本大学许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