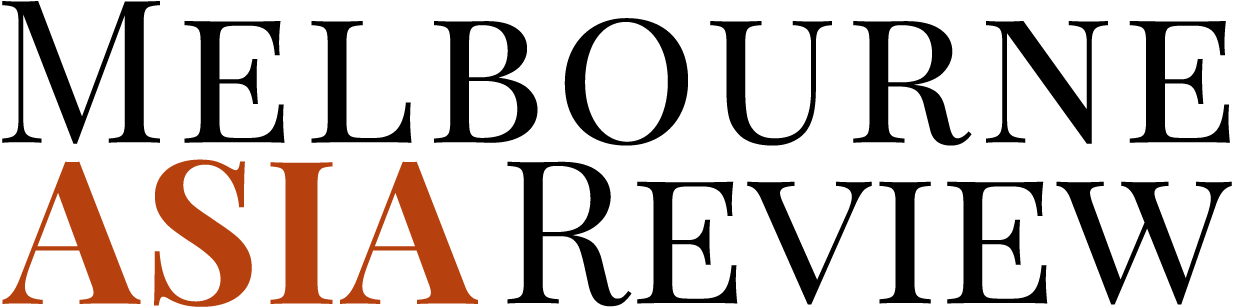译者:高瑞欣(Ruixin Gao)、李越(Yue Li)、刘钰(Yu Liu)
翻译审校:魏安天博士(Dr Anthony Williams)
当代海外族群的跨国网络的规模比以往更庞大、流动性更强。这些网络的存在意味着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在语言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这种语言多样性虽然丰富了当地社会,但同时也带来了某些包容性和公平性方面的问题。
与此同时,英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如果一个人不会说英语或其本国的主要语言,那么他们可能会在建立并维系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方面遇到困难。
英格利特·皮勒(Ingrid Piller)是悉尼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应用语言学的特聘教授。她是一名社会语言学与跨文化交流的国际公认专家,广泛研究并撰写有关语言多样性、社会劣势和社会公义的学术文献,探讨语言如何与权力、身份和不平等之间的相互作用。
下文是关于《墨尔本亚洲评论》(Melbourne Asia Review)的责任编辑凯茜·哈珀(Cathy Harper)对皮勒教授的采访。
英语是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但它会有什么压制性的影响吗?或者说它会对其他语言和文化产生什么压制性的影响吗?
大家都说英语是全球通用的语言,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虽然全球各地的学校都教授英语,但世界上大部分人实际并不会说英语。而且,即便人们在学校学习过英语,这也并不代表他们能用英语自如交流,或处理重大的事情。通常,那些英语说得非常好的人(所谓的“母语者”),和那些英语熟练度较低、表达自己缺乏信心的人中间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在交流的时候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
在澳大利亚的语境下,这种情况是如何体现的?
我们最近出了一本书,叫《新语言中的生活》(Life in a New Language),是一项纵向民族志研究。我们调查了1970年至2013年间,抵达澳大利亚的130名来自34个不同国家的非英语母语移民者,考察了他们的语言学习经历。大多数参与者在抵达澳大利亚时已经具备相当不错的英语水平,这是因为申请澳大利亚签证时(比如技术移民签证或学生签证),需要证明具备相当高的英语水平,通常是需要通过诸如雅思、托福等语言测试。因为他们的英语水平已经得到了测试机构的认证,他们就会认为:“正是因为我的英语这么好所以我才能拿到澳大利亚的签证。”但是,在真正抵达澳大利亚之后,他们往往会感觉自己什么都听不懂,在口语方面很吃力,而因为大部分人在海外学习的英语是英式或者美式英语,对他们来说,澳式英语特有的一些表达尤其带来困难。他们无法进行交流就意味着他们难以租房、找工作和签订电话合同,因此可能会失去信心。
我们的研究还包括许多来自后殖民国家的参与者,主要是非洲,在这些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英语也是授课语言,而对于这些参与者来说,在日常生活中用英语交流并不陌生。但是,他们来到澳大利亚后又发现自己的英语被“贬低”了,他们被当作不会说英语的人,对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来自亚洲的参与者情况略有不同。由于大多都是技术移民,与那些难民背景的人的情况相比,确实存在差异。有几个亚洲女性是持旅游签证或打工度假签证来澳大利亚的。例如,一位来自日本的女性,我们就叫她纪美子。她花了10年的时间环球旅行,曾经在英国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在澳大利亚旅游和工作了一年。后来她遇见了一位澳大利亚男子,与他相恋,并想留在澳大利亚。她虽然以前成功从事了一份又一份的工作养活自己,但婚后她想发展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她投递了各种工作简历,但收到的回复寥寥无几,而且那些有回复的雇主认为她的英语不够好。之后,她决定转行,接受了儿童保育员的培训,但在培训结束后,潜在雇主仍觉得她的英语可能不够好。她彻底失去了信心,最终干脆放弃找工作的目标,并且决定回归家庭做一个全职妈妈。
亚洲女性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她们在海外培养的专业技能在澳大利亚往往难以得到认可,如果在海外取得了某一资格,到了澳大利亚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获得认可。因此,存在一种反常模式,那就是这些女性来自性别平等意识被普遍认为低于澳大利亚的国家,但在澳大利亚反而需要更加依赖男性。
您能谈谈在这种情况下性别、种族和阶级之间的交集吗?
语言本来就不是孤立运作的,而英语能力不足很容易被用作不雇佣某人的表面理由,但背后的实际原因与种族歧视有关。在我们的研究中,有不少参与者反应他们因为不是白人而曾被质疑英语能力不足。澳大利亚社会中有一种刻板印象:只有白人才会说英语。有许多心理语言学实验证实了这种现象,例如,有一项研究表明,当 人们的视觉感知与听觉印象冲突时,视觉感知会占主导地位。这种现象被称为“麦格克效应”(McGurk Effect)。在关乎外貌表征的语境下,有一项著名的研究,在研究中录制了一段以标准的美式口音的英文讲座,并将它播放给两个本科生小组。播放录音的时候,给两组学生分别配上了白人女性和亚洲女性的画面,那就是说一组学生以为演讲的人是一位白人女性,而另一组学生以为是一位亚洲女性。听完了录制,学生们需要填写一份关于这个讲座的问卷。那些以为是在听白人女性演讲的学生认为:“讲座内容非常清晰,我都听懂了,结构有条理,学习体验也不错”。不过,那些以为是在听一位亚洲女性演讲的学生就给了不同的反应,虽然听的是一模一样的内容,一模一样的录制,他们就认为:“由于老师的口音,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演讲内容不清晰”,并将学习体验评为“较差”。明明是相同的标准美式口音,但结果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实验就证明了人们用眼睛来“听”。
我们的研究着眼于这个现象的日常表现形式,探讨这个现象对于“听”起来像亚洲人的移民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生活在澳大利亚亚洲形象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人们的语言学习过程中,特别是就业方面,是如何体现出来的。正如我所说过的,有许多人向我们反馈了负面的经历。
哈珀: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应对这种情况呢?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但你认为有哪些可能的解决办法?
这其实是我们真正需要提出的问题,因为在当下的社会中,我们并未认真对待语言多样性。人们来到这里学习英语,在家中仍然使用其他语言,但从公共视角来看,我们是一个英语单语社会,而这种意识形态对那些出于各种原因英语没达到母语水平的人和那些被视为英语说得不好的人来说,会带来负面影响。
我们需要做的是更充分地认识到,我们不仅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多语种社会,如果接纳多元文化,同时也需要认真对待语言现实。社会中的语言维系具有重要价值,不仅有助于维持社群认同,这本身就十分重要,还有助于促进社会凝聚力。如果移民的第二代不再使用他们的家传语言,那个家庭中长辈和晚辈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尤其在父母步入老年后,长辈与年轻一代之间会出现明显的沟通障碍。此外,语言维系在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对我们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地位具有重要价值。我们的社会本身拥有语言多样性,却没能加以维护,因此学校最终培养出的是只掌握单一语言的学生。事实上,要支持儿童发展多种语言能力,并不需要投入太多,只需适当的规划与引导即可。
除了认识到语言多样性之外,我们最需要改变的其实是教育政策。具体来说,就是要将外语学习纳入中小学课程。在这一点上,澳大利亚的确落后于世界很多国家,因为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学生在学校教育体系中至少要学习一门外语。教学大纲里也有足够的空间支持学习一到两门外语并学到高水平——在芬兰,学生甚至要学习五门外语!而在澳大利亚,我们却一直没有真正推动外语学习这一事。如果在学校里没有学习某种语言,即使在家一直在使用这门语言,仍然会缺乏相应的学术语言能力。通常来说,在学校里没有系统地学过这门语言,往往无法掌握阅读和写作能力,这两种技能正是拓展语言能力的关键。我们需要在学校体系中,为学生学习英语以外的语言提供支持,使他们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通过教育体系维护学生的家传语言。这就是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地方,如果实现这些变化,将在文化、社会凝聚力、包容性、商业及外交等多个领域带来诸多积极的连锁效应。
你认为刚提出的这些教育体系上的改变,是否有助于应对澳大利亚社会中潜在的种族主义,以及人们对他人英语水平高低的主观臆断?
这很难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而且多元文化备受推崇,但这是个忽略语言的多元文化主义。有过学习一门外语的经历,会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理解那些在学英语时遇到困难的人。有时候,人们会因为对方不懂英语而感到不耐烦,并倾向于认为这是学习者自己的错。不论遇到怎样的语言问题,我们都会倾向于把问题归咎于语言学习者,认为是他们学得不够好。许多澳大利亚人从来没有过在异国他乡用外语生活的经历,所以我认为他们并不了解用一门无法轻易脱口而出的语言生活有多艰辛。如果我们的学校能提供更好的外语教育,我想我们大概也会多一些同理心,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如果澳大利亚在教育体系中优先发展一到两种英语之外的语言,比如日语和中文,这是否会总体上削弱非英语语言的关注度与活力?
我不这样认为。目前我们是在优先使用英语,所以你提出的观点——就是如果没办法为所有语言提供服务,就干脆一种都不提供——我并不同意。
在中小学时期,应该优先发展几种外语,因为这需要配备合格的教师和充足的资源,而且不能频繁更换,必须保持一定的连贯性。我认为,澳大利亚外语教育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变动太多。落实语言政策需要长期的投入,因为培训教师、开发优质教材以及与合作院校建立伙伴关系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在这些方面变动过频繁,就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我们需要克服这种短视思维。
理想的情况可能是,澳大利亚在学校体系中优先发展一两种外语,这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类似。当然,其他国家优先选择英语作为外语,所以要优先发展哪些外语是个更容易做出的决定。比方说,在中国、韩国、日本和欧洲所有国家(英国除外),除本地语言和国家语言之外,学校体系中首先教授的外语都是英语。英语国家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需要根据哪些外语更具优势来做出选择。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应该优先选择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中文,但也可以选择其他语言,比如澳大利亚传统上教授的外语,就是欧洲语言、日语、印尼语等等。不同的州和不同的地区可以根据当地情况选择一门、两门或者三门外语,并为这些外语提供优质的教学项目。
此外,还需要由社区学校开设语言课程。从国家层面来看,大多数语言并不是随机分布的,而不同社群集中于不同特定的地区和区域。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比如说,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开设阿拉伯语课程,在另外一个区域开设日语课程,或者在越南裔聚居的地区开设越南语课程。这种方式可以在地方层面为家传语言使用者和其他感兴趣的人提供优质语言项目。
英语在澳大利亚的主导地位也极大地影响了原住民语言。非常希望听听你对此的看法。
说到原住民语言方面,澳大利亚不同地区的原住民语言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在澳大利亚某些地方——尤其是北领地和南澳大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州的部分地区,原住民语言及克里奥尔语言(creole languages)仍然活跃,并在不同社群中被广泛使用。在仍然使用原住民语言的社群中,我们需要确保学校提供双语教育项目,保证当地儿童不仅保留他们的母语,也能掌握高水平的英语。北领地曾经推行过针对原住民语言与英语的优质双语教育项目,然而,近年这一项目越来越被削弱,现在又回到了英语优先的状态。世界各地的众多研究早已表明,以母语开启正规教育是提升少数群体儿童的教学成果的关键策略。否则,对他们来说在学校就会经历一种“自力更生”的教育体验,能否成功全靠自己摸索。早期儿童教育应当优先采用母语教学,例如在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阶段,大约80%的教学时间应使用学生的母语授课,之后再逐步引入英语作为正式学习语言,并在之后逐步过渡,减少母语教学的比例,增加英语的比重。这种模式被认为是少数群体教育的最佳选择。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种教学模式自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一直在北领地推行,直到最近才开始逐渐削弱。由于这个议题经常被当作所谓“政治足球”(那就是说经常受各方争论和推诿),现在母语教学已经逐渐消失,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基本上就是全英语授课。这对教育成果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试想一下,一个刚入学的小孩不仅要学习新的知识内容,还必须以自己尚未掌握的语言去学习,这无疑是“双重挑战”:既要学内容,又要学语言。
在维多利亚州大部分地区和墨尔本等地,情况有所不同,原住民语言已不再被广泛使用。我认为,在那些地方,目前有很多社群希望恢复他们自己的语言,也有一些很不错的原住民语言复兴项目。无论如何,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应该学几句原住民语言,至少学会用他们所在土地的当地语言表述“对原国土地的礼敬”(Acknowledgement of Country)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词汇。我认为,这不仅意义深远,还会有助于与原住民的和解。
中文正在塑造中国以及海外华人社群的文化认同。你如何看待中文与英语和其他语言在全球语境中的互动?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显然,中国的崛起带动了中文的崛起,我们在全球某些地区确实看到学中文的人数显著增长。尽管在澳大利亚并非如此,但在非洲以及南亚、东南亚的不同地区,中文越来越受欢迎。这一直是语言的历史规律,语言的兴衰往往与其使用者的国力强弱息息相关。从长远来看,所有曾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语言最终都会衰落。比如,如果我们回顾拉丁语的历史就会发现,在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的影响下,拉丁语曾一度成为欧洲所有人都学习的语言,地位堪比今日的英语。但如今,几乎没有人学习拉丁语,它已经成为一种一般只用于学术用途的死语言。如果人类还有希望应对气候变化、继续存续下去的话,我确信英语最终也会经历同样的命运。下一个全球语言是否会是中文,我们目前还尚难定论,但学习中文的人数相较以前的大幅增加确实是事实。英语的优势是它被广泛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对象,也就是说,英语的掌握者早已不局限于母语使用者。正如我之前所说,实际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的母语使用者如今仅占全球英语使用者的少数,而全球大部分英语使用者为了学习英语已经做出了“大投资”,因此,他们当然希望维护英语的主导地位。学习一门语言是十分困难的,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这无疑都是一项巨大的投资。正因如此,全球许多投入大量资源的英语学习者都在竭力维护这项投资的价值,因此我们还可以预见英语继续保持主导地位的未来。尽管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为了顺应全球的发展趋势,在学习中文,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中文的第二语言使用者仍占极少数,这正是中文与英语之间的真正差距所在——大多数中文使用者是母语者,即使在全球南方对中文的兴趣不断攀升,真正后期学习中文的人仍然仅占极少数。因此,我认为,目前来说,英语的主导地位并不可能被中文取代。
哈珀:最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墨尔本亚洲评论》这一期的主题:怎样才能避免语言边缘化现象?
皮勒:教育体系至关重要。我刚刚提到,学习一门语言是一项巨大的投资,我们的社会需要做好准备,在下一代还小的时候,就开始投资学校教育。我们送孩子去学校,是为了让他们学习知识,为成年生活做好准备,因此,确保语言学习在学校中拥有重要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是最关键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举措,比方说,用各种方法来增强边缘化语言的“能见度”,比如在街道标志上增加边缘化语言、设置双语街道标牌,或者使用原住民语言来标识原住民所守护土地的各个区域。既然我们用街道标牌来标识区域,为什么不采用双语形式呢?事实上,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积极的努力,现在许多机场会标出原住民语言的地名,比如Narrm(墨尔本)——这就是一种增加边缘化语言“展示机会”的方法。我认为同样的做法也适用于移民语言,在悉尼的哈里斯公园区(Harris Park,亦称“小印度”),旁遮普语(Punjabi)的“能见度”正迅速增加;而在温哥华的类似地区,街道标牌上有英文和旁遮普语的双语标识。这是一个简单的举措,既作为对另一种语言的认可,又防止它边缘化,这种认可意义重大,具有重要的象征价值。不过,我认为和教育体系的改变相比,这些措施只是辅助性的手段。
英格利特·皮勒,唐娜·布托拉克,艾米莉·法瑞尔,洛伊·李星,希瓦·莫塔吉-塔巴里,薇拉·威廉姆斯·泰特.《新语言中的生活》(Life in a New Language).
图片:墨尔本博士山(Box Hill)购物中心的人群。来源:Alpha/Flickr。
原文发表于《墨尔本亚洲评论》第二十一期,2025年3月3日
原文DOI:10.37839/MAR2652-550X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