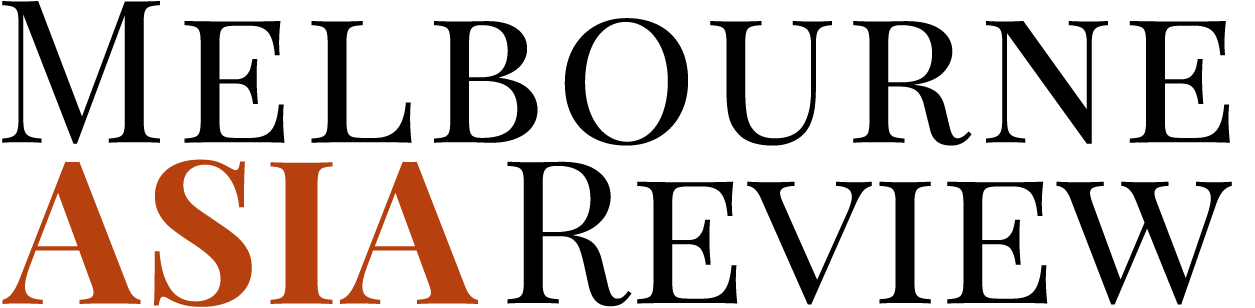译者:邵之晗、大海Alexander Dalla-Riva、许若寒、查婉晴
归属感
虽然归属感无法简化为“家”的概念,但两者在不断变化的全球政治环境中的流动性和移民体验研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大卫·诺兰(David Nolan)、凯伦·法夸尔森(Karen Farquharson)和蒂莫西·马乔里班克斯(Timothy Marjoribanks)在其2018年编辑的文集《澳大利亚媒体与归属政治》中,首先对澳洲航空的广告活动“感觉像家一样”进行了批判性研究。该广告于2014年首次推出,以“真实”的人回到澳大利亚为主题,将澳大利亚定位为“家”和“我归属的地方”。2015年广告中描绘的“家——我归属的地方”是以中产阶级、世俗和白人为主的。这个“家”象征着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本身,在这里,“非白人和土著居民、城市和工人阶级的生活场景以及与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相关的非‘英式的‘(盎格鲁 Anglo)文化传统和仪式的存在”在广告中未有体现。这种缺失意味着他们被排除在作为家园的国家之外。
2023年5月,澳航再次推出了“宾至如归”(Feels like home, again)系列。在因为“新冠疫情”(COVID-19)大流行而封闭边境的时期过去之后,一个儿子四年来第一次从东京回到墨尔本。对澳大利亚内陆的怀念,以及“澳大利亚妈妈”和海外儿子之间“现实生活中的重聚”,预示着在多年的边境关闭之后,旅行安全回归正常。
归属感具有时间性、空间性和交叉性。而且,大流行病带来的全球不确定性/流动性使我们不得不停下来,重新审视对归属感的普遍理解,即归属感是建立在“对‘家的感觉’的情感(甚至本体)依恋” 之上的。我们只需反思一下,当大流行病开始蔓延时,时任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是如何指示许多留学生(其中大部分来自亚洲国家)和临时访客“是时候回家了”。这种“回家”的指示模仿了种族主义者“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去”的陈词滥调,并向接受者发出了他们不属于目前居住地的信号。
在全球疫情期间,中国恐惧论和反亚裔种族主义以一种肉眼可见的新形式愈演愈烈。澳大利亚的亚洲女性遭到性骚扰的事件显著增多;在澳洲社交媒体上,亚洲年轻人参与新冠疫情相关内容较多,也更容易受到反亚裔情绪影响。在疫情之中死灰复燃的中国恐惧论在作为殖民移居地的澳大利亚有着很长的历史。吉尔伯特·卡鲁亚(Gilbert Caluya)对20世纪90年代参议员宝琳·韩森(Pauline Hanson)将“国家”称为“家”的研究表明,将“国家”与“家园”混为一谈助长了种族主义言论,重新将白人的民族归属感作为中心并重新赋予其特权。卡鲁亚提出,这种对家庭亲密关系的批判性解读并不否定移民找到归属感和创造家园的方式。
“家园”的可塑性使其从个人的家庭延展到邻里、社区和国家,格雷格·诺贝尔(Greg Nobel)所做的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其研究2001年之后澳大利亚移民所经历的反穆斯林与反阿拉伯种族主义。在许多受访者看来,“家园”给了他们一点喘息之地,将那些老套的种族歧视言论隔绝在外。家园之内的私人物品促成了“家园”即为“舒适场所”的概念。针对安东尼·纪登斯(Anthony Gidden)的“本体安全论”,诺贝尔认为家园是安全感的中心,我们依靠家园带来的安全感维持“自我意识”,也就是维持“身份、关系和归属感”。
监管和维持松散的归属感边界不仅要取决于社会阶层,还会沿着“国籍、民族、‘种族’,性别、阶级、宗教、年龄和性取向等多重交汇与分歧的轨迹被塑造”。个人在这一系列权力体系内部可能会采取一种务实的、将自己归属于某个群体的策略,由此主张自己享有相应群体的“权利”。里米·汗(Rimi Khan)认为,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青年的人口普查中,年轻人在采访中的讨论里表现出的强烈国家归属感是可以理解的。受访的年轻人对他们的言论可能被有心人利用表示理解,这使得他们与通过寻求归属感来对抗“种族主义的排外效应”。
安全感
在新冠疫情封城期间,“居家隔离”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安全”。对许多人来说,在疫情大流行的封城期间,家的含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在封城期间,一个人的住所同时也是工作场所、学校和咖啡馆。许多人还被要求离开家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工作。家作为一个安全的地方衍生出了很多引申义,然而,家不是一个对所有人来说一直安全的地方。由于人们对家中不安全的意识有所提高,因此公共信息表明,即如果由于家庭暴力等原因导致家庭环境不安全,可以选择离开家。
在被称为“家”的空间里,人们可能会产生孤独感。一项研究旨在了解年轻人体验孤独感经历,研究者要求来自伦敦的黑人、亚裔和其他少数种族群体表达他们对家的概念。这项研究跨越了疫情前和疫情期间,他们发现,不管是疫情前还是疫情期间,年轻人都将孤独感与家联系在一起,但在疫情期间,受试者对家的概念持有更消极的态度。
家的形象往往蕴涵归属感,家是属于自己的地方,也是让人感到安全可靠的地方。一般来说,安全感与归属感一样,也是一种与人、空间、物体和环境之间的主观情感关系。“安全感”的概念不是客观决定的,而是主观感受到的,要理解“安全感”的概念,就必须理解“安全感”的空间和时间背景。虽然一个人可能在某个特定地点、空间或场所感到安全,但另一个人可能在同样的地点、空间或场所会感受到特别不安全。
对“安全感”和“归属感”的进一步探索
本期《墨尔本亚洲评论》中的文章针对亚洲及其周边地区的流动性、归属感及安全感,以及性别、性和性取向的交互影响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这些文章着重突显了在探讨个体如何应对多重歧视时,基于社区以及共同创造方法的重要性。为在澳大利亚高等院校的国际学生创造和持续提供安全区域(李冬梅Dongmei Li, 希蒂·努鲁尔·穆纳维拉·莫哈末·罗斯兰 Nurul Mohamad Roslan, 张沛涵Sally Pei Han Chang 和 朱涛Zhu Tao),以及为在日本东京的难民提供以学生为主导的支持网络(克里斯蒂娜·福冈Christina Fukuoka 和大卫·斯莱特 David Slater)。这两者的难度和重要性强调了提高不同发声和经验的重要性。由于当代权力结构受到推崇,性种族主义(吉尔伯特·卡鲁亚Gilbert Caluya)也在持续发酵,种族和性别结构不平等(莫妮卡·维纳尼塔Monika Winarnita 和卡梅拉·利昂 Carmela Leone),无论是在学习空间领域(福冈和斯莱特;李冬梅等人Fukuoka and Slater; Li et al)还是在数字信息技术(埃尔文·查尔斯·卡巴尔金托Earvin Charles Cabalquinto),空间都可以用来促进远距离人群的联系感(雷努·辛格Renu Singh),并在紧急时刻提供重要的 “生命支持”(维纳尼塔和利昂)。这种距离可以形成一个“悬浮区”,在这个“悬浮区”中,流动性可以创造“酷儿的生活和身份”(弗兰·马丁Fran Martin)。如何驾驭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度和法律框架的影响。C.L.奎南(C.L. Quinan)和亚当·陈·戴德玛(Adam Chen-Dedma)表明,亚洲地区在承认跨性别和不同性别身份方面,其进步与偏见并存。苏吉斯·库马尔·普兰库马尔(Sujith Kumar Prankumar)、王梓浩(Horas TH Wong)和毛丽明(Limin Mao)对当代澳大利亚亚裔男同性恋群体感染艾滋病毒的结果进行了分析,主张采取一系列将法律卫生和社会关怀结合起来的干预措施,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本期文章吐露了为何一些群体会处于多重压迫轴线的“交汇点”。它们还展示了如何创造性地利用虚拟和现实空间,在原本孤立和/或歧视的环境中提供支持。每篇文章都提供了潜在的新框架,以探讨性别如何影响亚洲及其周边地区的流动性、归属感和安全感。
图片提供者:厄兹格·塔什克兰(Özge Taşkıran/Pex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