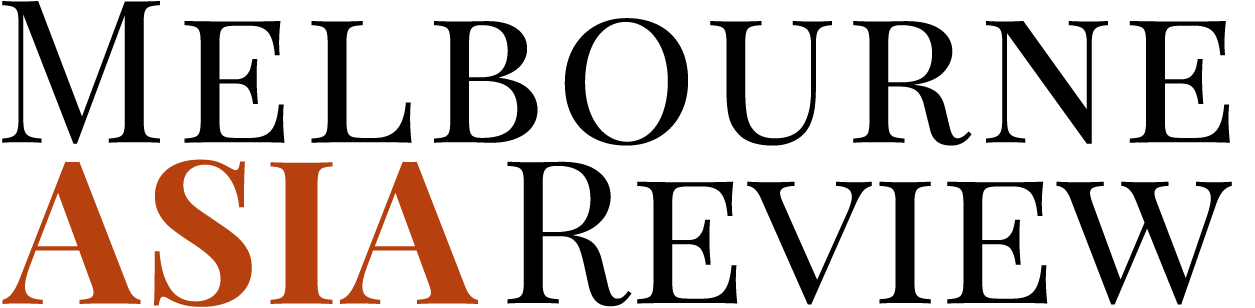译者:陈鸿武(Eric Chen), 周倬男(Zhuonan Zhou)
自2019年12月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关于其对种族或性别歧视的影响的研究不断涌现。然而,讨论疫情相关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交叉性的研究甚少,亚裔女性的遭遇被大众忽视。
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我们于2021年底对20位居住在维多利亚州——澳大利亚人口第二大州——的亚裔女性进行了采访。我们分析了以下问题:
- 亚裔女性在澳大利亚是如何遭遇种族歧视的;
- 她们所遭遇的种族歧视又如何与性别歧视交叉;
- 她们如何看待自身的遭遇,以及未来遭遇类似情况时她们会如何应对;
我们还论证了以下三点:
- 对亚裔女性遭遇疫情相关的种族歧视缺乏关注,掩盖了亚裔女性比亚裔男性遭遇更频繁的种族歧视这一事实;
- 对性别歧视与亚裔女性所遭遇的种族歧视的交叉性这一问题缺乏关注,使得她们更加难以理解自己的境遇,且难以阻止不善对待行为继续发生;
- 受访者的反映表明,一般有色人种女性更有可能基于共同遭遇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而结成同盟,这对女性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的研究和倡议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作为一位在澳大利亚居住多年且亚裔外貌特征明显的女性,我时常觉得自己比我的非亚裔女性朋友和亚裔男性友人更脆弱。我也意识到,自己身材较为娇小,面容更显年轻,这也加剧了我的焦虑。自新冠疫情以来,我跟所有人一样,都很担心会感染新冠病毒。但是,同时我也感到非常焦虑,担心自己成为种族歧视的目标,也担忧那些和我一样的人也会受到种族歧视;同时,我还常常遭到性别歧视。对我来说,亚裔女性移民在澳大利亚遭遇类似情况,我早已不觉得惊讶。在新冠疫情期间,这种情况更是有所加剧。
出生于亚洲的澳大利亚人口数量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9.9%。在最常见的十个海外出生国中,有六个是亚洲国家(印度、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此外,出生于亚洲的澳大利亚人比出生于其他地区的澳大利亚人年龄更小,且亚裔澳大利亚人通常都接受过高等教育,许多人还凭借他们的学历移民至澳大利亚——这也是澳大利亚优先考虑技术移民的严格筛选移民政策之一。
我和本文的二位合著作者为此采访了19位自我认知为亚裔移民的女性以及一位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亚裔女性。受访者在受访期间均居住在维多利亚州,年龄在21岁至49岁之间。其中大部分受访者接受过高等教育且至少拥有高等教育文凭。她们出生于新西兰、英国、中国大陆、印度、马来西亚、尼泊尔、新加坡、韩国、斯里兰卡、日本、柬埔寨与台湾。本文中所有名字均为化名。
受访者在澳大利亚遭受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经历大有不同,有人从未经历类似遭遇,有人则甚至遭到了人身攻击。20位受访者中,有8位在新冠疫情期间经历过种族相关的言语侮辱或肢体攻击;有14位受访者聊到了作为定居在澳大利亚的亚裔女性而在疫情之前和疫情期间所遭受的性别歧视。
她们的种族歧视经历与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报道如出一辙,这反映了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群体的种族歧视愈演愈烈的情况。例如,邦尼(Bonny,20多岁,出生于马来西亚)向我们讲述了她和朋友是如何在街上遭到不善待遇的,原因仅在于她和她的朋友站出来回应了两位正在对路人进行种族歧视骚扰的女性,那两名女性向路人喊道 “滚回中国”。邦尼的朋友因此被其中一位施暴者攻击,而另一名施暴者向邦尼挥舞玻璃酒瓶以示威胁。
其他受访者,例如迪塔(Ditya,31岁,出生于尼泊尔)在疫情期间也有着类似痛苦且难忘的经历。她曾在墨尔本街头被施暴者冲着大喊大叫,说她来自另外一个国家,只不过是住在施暴者口中 “我们的国家” 澳大利亚而已。迪塔说:“那种感觉十分糟糕,我什么都没有回应,赶紧远离了,因为我感觉如果我回应了,他可能会有其他举动……或是骚扰我。”
我们向受访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澳大利亚,女性在面对种族歧视时,是否更加脆弱?”,迪塔贴切地回答道:“我认为是的,因为与男性相比,我们总被当作弱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不会站出来正面回应……我甚至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走开或是尽我所能避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被看作是弱者……我觉得……女性就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骚扰与畏惧暴力
本文中的受访者均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成为种族主义者攻击的目标。这与2021年的一份有500多位受访者参与的研究——《就新冠疫情期间种族歧视的调查》——结果相呼应。该研究发现,受访者中,经历过种族歧视的多为女性(占60.1%),而男性只占34.1%。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我们的问卷问题仍然集中在探究受访者在疫情期间遭受的种族歧视经历,但受访者们也经常表达她们对种族歧视、性骚扰、以及性别相关的暴力问题的担忧。根据受访者的反馈,我们注意到,尽管亚裔群体在疫情期间遭遇种族歧视的情况加剧,亚裔女性遭受的种族歧视的方式更加特殊,比如,在网络或是现实的骚扰中遭到性化。然而,我和我的合著作者均感觉到,本文的受访者无法从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交叉的角度来阐述她们的经历。
例如,菲奥娜(Fiona,29岁,出生于中国大陆)向我们透露,她自疫情以来,遭遇过多次的骚扰,其中包括陌生男性在半夜向她频繁打电话,她也收到陌生人的社交平台讯息并通过声称会说中文试图与她交友,也曾遇到陌生人在公交车站用中文跟她搭讪,试图 “勾搭” 她。她觉得她被盯上是因为这些男性认为中国女性更容易搭讪,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女性会觉得拒绝是不礼貌的。用菲奥娜自己的话来说,这种经历让她觉得自己被物化:她自己更像是一个 “物品” 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每天都被物化与异化,这也使她对男性感到害怕。与其他受访者一样,菲奥娜不知如何更好地回应施暴者;此外,受访者们还经常用 “奇怪(的人)”一词,而非 “种族歧视者或性别歧视者” 来描述她们的经历和施暴者。
与之类似,简(Jane,26岁,出生于中国大陆)也因疫情以来的几次网络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开始担心会被男性攻击,比如在公共场合被陌生人冲着大喊大叫。简还分享了一次更为恶劣的网络骚扰经历:“有几次网络经历让我感到非常奇怪,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应对。自疫情以来,好几次有不同的人想在社交平台上加我为好友,他们都是男性。他们有些还对我进行口头骚扰,如‘嘿,美女’,这类猥琐信息,甚至是在社交平台上发送色情图片。”
随着疫情期间被骚扰次数的增加,菲奥娜和简的担忧有所加剧。她们的经历也表明,亚裔女性确实更容易成为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目标,同时她们也感到更为无力。简和菲奥娜都无法理解她们为何被骚扰。她们的经历与她们身为亚裔女性的身份却是紧密相连的:她们的外貌被他人定性,因此不论是由于性别还是种族原因,她们似乎都很容易成为目标。正如简所说:“假如我的外貌不是这样,假如我来自不同的种族背景,那我可能不必承受这一切(暴行)。”
亚裔女性通常身材娇小,长相年轻
我们的研究发现与其他研究发现有所不同,例如有研究发现澳大利亚原住民受访者均认为正面回应种族歧视者是件好事,但我们的受访者却表达了相反的观点。
作为亚裔女性,多数受访者觉得自己在面对施暴者时倍感无力,无论是因为她们的娇小体型还是因为她们更显年轻的外貌。洛丽(Lorrie,30岁,出生于中国大陆)强调道,较她而言,她所遭遇的白人女性施暴者身材高大,她会因害怕受到人身攻击而选择不予以回应。黛安(Diane,40多岁,出生于新加坡)也认为亚洲人看上去更容易受伤害,她说道:“我身材娇小,只有1米5。我甚至没有像大多数当地女性一样身高达到1米6。”黛安还提到,如果她遭遇了种族歧视事件,她会立刻逃离,而不是正面回应施暴者,因为她觉得自己身材过于娇小。菲奥娜则是向我们介绍她更显年轻的外貌是如何成为受攻击的原因的。她说道:“作为一个长相更显年轻的中国女性,正面回应是非常困难的;想要真正塑造一个强大的形象来回击也非常难。” 相反,她聊到了她是如何需要保持 “敏锐” 并 “利用”可用资源来回击,而不是只靠自己(战斗),因为单靠自己会感到非常不安全。
人们对于亚裔女性柔弱、顺从的形象和她们避免矛盾冲突的文化习惯所产生的刻板印象,也是使受访者们感到更加脆弱的原因。例如,桑尼(Sunny,20多岁,出生于新加坡)曾在墨尔本街头遭受了种族主义者的攻击。关于是否觉得亚裔女性相比于其他女性更容易成为种族歧视的对象这一问题,桑尼作出了回答,她说道,人们对亚裔女性柔弱和顺从的刻板印象导致许多人认为她们 “好欺负”。同时,桑尼也承认了在文化层面,她也被教育要 “避免冲突”。
“我认为有色人种都或多或少会遭受种族歧视,但是我认为如今的形势矛头则指向了中国人,原因或许是新冠病毒以及中国共产党。谈起亚洲人,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人……我认为对于女性是柔弱且顺从的刻板印象在亚洲文化里是根深蒂固的,因为我们的体型,许多人认为我们更娇小并且好欺负。在亚洲媒体,甚至是故事书中,我们经常被描述为弱小的女性,无法为自己争取权利,无论是在精神方面还是身体方面……我从小就被教育不要攻击(批评)别人,必要的时候要避免矛盾冲突。但那些施暴者们并不这么想。在他们眼里,我们只是更加弱势、更容易成为攻击对象的有色人种罢了。”
桑尼的回答指明了有色人种都很容易遭遇种族歧视的事实,只是在这个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刻”种族歧视的矛头更多地指向了中国人和亚洲人。不只是桑尼,其他的受访者同样反映,她们和其他族裔女性一样容易受到种族主义的影响。例如,黛安说道:“作为一个亚洲人,我确实在面对种族歧视时感到脆弱。但是我并不认为我比其他人(比如原住民女性)‘更加’脆弱。” 谭雅(Tanya)也说道:“就面对种族歧视时的脆弱程度而言,与原住民社群相比,我想说这取决于不同情况。我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经历着种族歧视。” 这些受访者们的回答都表明,这些少数女性群体团结一致是有可能的。
虽然大多数受访者们没有与那些施暴者们对峙,也没有向警方报案,但部分受访者表示她们今后会这么做。例如,迪塔认为她应该勇敢回应那个对她大吼大叫的男性,并让她的朋友报警。其他受访者,例如邦尼,向警察报案说她遭受了攻击,但是她发现警察也是种族主义者,警察对有原住民血统的施暴者发表了种族主义的言论。邦尼对澳大利亚整体人口背景进行了反思,她说:“那位施暴者很可能也是澳大利亚白人种族歧视环境下的产物。所以我们都是受害者,从受害者的角度来讲,她只是在食物链中处于底层。” 受访者们同时也讨论了她们如何避免种族歧视的策略。例如,谭雅说由于她在新冠疫情开始时遭遇过一次种族歧视的经历,以至于如今她对男性都特别警惕,尤其是在乘坐公共交通时。奥黛丽(Audrey)同样提出了一些策略,例如,规划时间去购物,以减少与 “年轻白人” 相遇,并且相比于亲自购买食物,她更倾向于网上点餐。
然而,除了未来举报类似的事件之外,受访者们更多注重她们的规避策略,而不是积极主动地解决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事件。我们认为,这些受访者们缺乏行动的现象与无法理解和定义她们遭受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交叉经历有关。
阐释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交叉联系
种族歧视经常与性别歧视交叉在一起。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交叉性常在性种族主义有关的研究中被谈论。性种族歧视的定义为:基于认知的种族身份,在潜在的性伴侣或情侣之间的歧视。然而,关于性关系中的种族偏好——即一个人对特定种族群体的人进行性亲密接触的偏好——却少有人提及。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亚裔女性(或男性)会受到白人的偏爱,因为这些亚裔群体有着迷人及顺从等高度被性化的刻板印象。另外有人指出,对亚裔女性有性偏好的男性可能是受反女性主义的驱使,他们渴望重返传统的性别角色,而这种角色则在有顺从心理的亚裔女性身上所体现。
我们认为,亚裔女性的柔弱和顺从放大了她们的吸引力,但同时也使她们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如马嘉兰教授在她对澳大利亚中国女性移民的研究中强调的那样,她的研究参与者都害怕遭受攻击的原因与刻板成见有关,东亚长相的女性更容易成为非亚裔男性的性取向目标,这些男性对自己成为亚裔女性的伴侣的可取性有着陈旧偏见。这些受访者们也表示,因为相较白人女性或是中国男性,她们 “本身体型较小、柔弱且无反抗能力”,这使得她们在面对攻击时更为脆弱。
亚裔女性经常与她们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经历作斗争,同时她们在试图理解和谈论这些经历时也付出了巨大的感情。她们所经历的是解释学意义上的不公正性,这种不公正性是指由于社会解释性共享资源存在偏见性缺陷,某人社会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被掩盖,使其自身无法理解——这种边缘化现象是以白人为中心的经历驱动的,其忽视了其他族群的视角。受害者无法理解自身遭受的不善对待,使得她们无法做出反抗并找出有效措施去阻止它。
正如之前谈到的,菲奥娜和简所承受的解释学意义上的不公正性非常严重。她们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只能用 “怪异” 或者 “奇怪” 这样的词语,她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施暴者。菲奥娜告诉我们,她现在甚至愿意假装自己是日本人,以此避免更多的骚扰和攻击。由于没有意识到针对亚裔女性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之间的交叉性,她只能减少回应并将自己假装为另一国籍的亚裔女性。虽然暂时否认自己的国籍能够帮助她在当时避免潜在的或进一步的骚扰,但菲奥娜的这种 “策略” 并没有解决核心问题——即针对亚裔女性的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交叉现象。事实上,菲奥娜之前认为作为日本人(而非中国人)可能会避免令人不适的谈话和潜在的种族歧视。这本身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法,但同时,这也体现了她们在理解骚扰事件层面的偏见性缺陷。
虽然,对白人男性的恐惧这一主题贯穿整个访谈,受访者们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来自其他人种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认识,这种经历很可能会被忽视。我们认为,以 “白人与其他人” 组成的重要二元结构同样是造成解释学中不公正性的偏见性缺陷。有研究人员指出,种族歧视的施暴者可以是任何种族,甚至也可以是同种族。即使中国/亚裔受害者和白人施暴者的设定存在一定的真实性,但仅根据这种设定去理解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会掩盖人们的视线,并且会造成解释学意义上的不公正。事实上,在一些受访者的经历中也存在这种误解。例如,邦尼和她的朋友所经历的种族歧视成为了新闻头条,且起初被媒体报道为白人施暴者与中国留学生的事件。实际上,邦尼和她的朋友都不是来自于中国,也没有任何中国血统,而且那名施暴者是一位原住民女性。
研究与社会运动的不足
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会运动与针对疫情期间种族歧视的研究有着相似之处,二者都缺少对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交叉性的关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的社会运动主要集中于针对文化与语言多样性人群(CALD)的种族歧视或者对女性的暴力。特定群体的女性在疫情期间的经历却很少受关注。
研究发现,很多交叉性研究不再针对以有色人种女性为中心的行动主义和基于单一群体的方法。疫情爆发期间,反种族主义活动掩盖了性别问题。而在此期间,强调针对女性暴力的社会运动也同样掩盖了种族问题。然而,有关于身份(人种、性别等)和交叉性的对话有可能会达成共识。在思考反种族主义的时候,认识到亚裔女性的交叉性经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团结起来组成文化与语言多样性群体或是 “亚裔” 社群。相反,这种交叉性会成为多文化多语言的女性群体团结起来的基础。新冠病毒的爆发可能加剧了种族主义的趋势,但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契机,让人们在交叉性的基础上重新思考种族、性别和未来的结盟这些问题。
例如,邦尼反思了其在澳大利亚经历的种族歧视,她说那位攻击她的原住民也同样是一位受害者,她可能也经历过种族歧视。事实上,在白人认为原住民的性机制是 “原始的” 且其很少有性压抑这样的背景下,其他少数族群的女性比如原住民也遭受着种族化和性化的影响。亚裔女性柔弱和顺从的刻板印象与受访者们认为她们特定的 “缺点” 紧密相关——身材娇小、容貌年轻和避免矛盾的文化性格。然而,对于一些受访者来说,比如桑尼,她意识到有色人种在面对种族歧视时都更脆弱,而且只是因为在当前这种特殊的 “时刻”,中国人和亚裔人群成为了特殊的目标。
回到研究交叉性的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上,许多交叉性研究已不再针对以有色人种女性为中心的行动主义和基于某个单一群体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必须加强对亚裔女性的这种交叉性经历的关注,以使这些受害者们能够拥有共享的社会资源。只有当她们的社会经历不被以白人中心的经历所掩盖的时候,她们才能识别、抗议并阻止这种不公正的行为。在没有新冠病毒的未来,她们能够识别自己经历的能力将会让她们与其他有色人种的女性更加团结。
作者:汪诗薇博士(Dr Sylvia Ang),宋智英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Jay Song),潘秋萍博士(Dr Qiuping Pan)
图片:墨尔本维多利亚女王市场。资料来源:雅虎网络相册